中华素食文化小史
如若下番考据的功夫来看,素食的传统在中国可以从梁武帝萧衍讲起。这位虔诚的佛教徒曾颁布了《断酒肉文》。在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也已经提到了一些素菜的制作方法。到了唐代有了花样素食。北宋都市中出现了市肆素食,有专营食素菜的店铺,《梦粱录》中记载,汴京城内的素食多达上百种。明清时,素食的发展可谓生机勃勃,尤其到了清代,素食终于形成宫廷素食、寺院素食和民间素食三大支系,如今也被人们简称为宫素、佛素和民素。清宫紫禁城中,御膳房专设“素局”,可制作200多种美味素菜。寺院菜则或称佛菜、释菜、福菜,僧厨则称香积厨,已能配成品位甚高的全素席。寺院香积厨挖空了心思,可以用白萝卜或茄子加发面等原料制成“猪肉”,可以用豆制品、山药泥烹制出“油炸鱼”,可以用绿豆粉掺水仿制成“鸽蛋”,用胡萝卜加马铃薯仿制成“蟹粉”。民间素菜则在各地市肆菜馆制作,形式上更为随意。而究竟这里面的口味有何不同,也只能完全凭想象猜测了。
中国的饮食文化,很大程度上就是“写食文化”。这份对素菜的情有独钟,在文人墨客留存的篇章中也比比皆是。宋代陆游有诗云:“采擢归来便堪煮,半铢盐酪不须添。”清初李渔的《闲情偶寄》中言,“吾谓饮食之道,脍不如荤,荤不如素”,又言“草衣木食,上古之风,人能疏远肥腻,食蔬蕨而甘之,腹中菜园不使羊来踏跛。是犹作羲皇之民,鼓唐虞之腹……”吃素至此已经到达了一种如沐春风的境界。而屈原的“朝饮木兰之坠露,夕餐秋菊之落英”,把吃素上升到一种高雅芳洁、遗世独立的精神品质。民初的词人吕碧微更远赴巴黎参加欧洲素食主义大会,讲解中国的素食文化和传统,反响如潮。
素菜究竟算不算得上一种菜系,这个倒无从考证。事实上,为了把清新寡淡的素菜做得活色生香,大厨们恨不得南北交融,中西合璧,把一切菜系兼收并蓄。素食贵在鲜。从食材上来看,春之青蒿、野荠,夏之嫩豆、新茄,秋之白藕、红菱,冬之肥茭、鲜韭,古人讲究的这份时令,现在早已被高科技打破,各类食材一年四季丰富供应。除了蔬菜瓜果,各式菌类以及最具中国特色的豆腐和豆制品是当仁不让的主角,而且少不了的还有各色面点。从做法上,素菜制作的考究绝不亚于荤食,正所谓“一瓜可做数十肴,一菜可变数十味”。 如同在书法中最难写的是“一”字,如何将素食做得曼妙,对于色、香、味的把玩足以见得几分功力。
说起作为主料之一的豆腐和豆制品,最大的用处无外乎是“仿荤”。所谓的“以素仿荤”、“以素托荤”、“素质荤形”,对荤食模仿得愈像,技艺愈为人称道,食客们也是大饱眼福加大快朵颐。“素菜荤做”的技艺如果再细分的话,通常还有三种名头:一为“卷货”,即用油皮包馅卷紧,以淀粉勾芡,再烧制而成,比方说素鸡、素酱肉、素肘子、素火腿等;二是“卤货”,以面筋、香菇为主料制成,有素什锦、香菇面筋、酸辣片等;三是“炸货”,过油煎炸而成,有素虾、咯炸盒等。而且不单单是素料荤制,菜名也取得荤。上海玉佛寺的素斋,有名的几道菜红梅虾仁、银菜鳝丝、韭翠蟹粉,丝毫读不出半分素意。
正如中国人讲求中庸之道,在饮食上同样讲究荤素搭配。如今的仿荤菜大行其道,更多是因为“纯素”无法满足人们的口腹之欲。京城的一家素菜馆“天厨妙香”的老板告诉我,人们习惯的其实是调味料的味道,而并非肉本身的香味,这也是仿荤菜可以以假乱真的原因。
以“荷塘月色”为代表的一些“新派素食”,则在一些做法上热情的拥抱了西餐,大部分菜加入咖喱、奶酪、植物奶油来佐味。“踏雪寻梅”这道菜,主料是自制素鳗,而“雪”就是上面浇入的鲜奶油。“罗马假日”则用薯粉制成,看上去甜腻的外表尝起来却是咸淡的味道。而灿烂的“毕加索阳光”,充溢着植物奶油的香味,黄金南瓜加入素火腿,外配爽口西兰花和奶酪来装点。最为著名是“水煮三国”,倒是应景了如今的无辣不欢,主料是素牛肉、素鱼片、素火腿、粉丝、海带,上面充斥着鲜红的碎椒。
西方世界里影响大多数人生活的快餐食品,也纷纷走向素食化。在美国,Burger King和Denny卖起了素汉堡,麦当劳在加州也尝试测试这种产品的销售状况。Pizza Hut在印地安纳州的Ft。 Wayne推出了黄豆起司披萨。这种模式化的产品一旦收到良好回应,想必很快会复制到它们最为倚重的消费市场——中国大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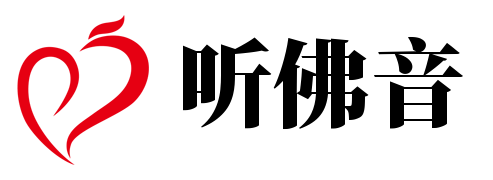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