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希那穆提的几次神秘转化经验(一)
摘自《克里希那穆提传》
1922年的年初,克里希那和尼亚搭船从科伦坡到澳大利亚悉尼参加通神会议。克里希那和赖德拜特已经十年未见,他似乎很高兴见到昔日的老师。在悉尼又不断有人指控赖德拜特的同性恋行迹,通神学会较严肃的会员因而大为不满,克里希那当时尽了最大的力量安抚这些人。
在悉尼他也见到了卫奇伍德。那时卫奇伍德已经是自由派天主教会正式任命的主教,1916年,他任命赖德拜特为自由派天主教会驻澳大利亚的区域主教。赖德拜特非常高兴,因为不但有任命仪式,还有豪华的圣袍可穿,同时还要诵念新编的英语祈祷文。
当时尼亚的身体仍然不太硬朗,会议结束以后,两兄弟决定绕道旧金山返回欧洲。通神学会驻美国的总干事威灵顿先生也在悉尼开会,他邀请克里希那和尼亚到加州奥哈伊住一段时间。那是一个靠近圣巴巴拉的印第安古城。当地气候干燥,对肺结核很有帮助。在他们离开悉尼时,赖德拜特从指导灵库特忽米那里得到一个讯息,深深打动了克里希那。
那是一段很长的旅程,尼亚上船后健康突然急速恶化,后来总算恢复了精神,不久他们便抵达加州。那是他们第一次游美国,克里希那对于乡间的美景十分入迷,有一回游毕红木森林,他禁不住赞叹那些神木如天主教的大教堂一般伟大。
克里希那和尼亚终于到达奥哈伊,他们住在一个木屋里,周围有六英亩的空地,后来安妮·贝赞特将土地买下送给两兄弟,取名为威哈拉,意思是高人的修院。
~~~~~~~~
每天早上克里希那穆提开始有规律地静坐,他很惊讶自己的心念反应竟是那么自在,他可以一整天专注地观想弥勒尊者。他形容自己在那期间愈来愈平静,愈来愈沉着。他所有的人生观跟着在改变,内心的门也开了。克里希那穆提在奥哈伊写了一封信给赖德拜特。
你是知道的,多年来我没有真正快乐过,我接触的每件事都令我不满,我的心智状态也十分凄惨。比起在澳洲时,我现在已经改变太多,我一直不停地思索当时从指导灵库特忽米那里得来的讯息。
灵性的觉醒
1922年8月,克里希那穆提突然进入激烈的灵性觉醒过程,从此他的生命便整个改观了。印度传统认为,瑜伽士如果深入探索迷津一般的意识领域,就有可能觉醒体内的识能拙火,全然不同的心灵现象就会产生。那是深入内心未知领域的旅程,拙火觉醒的瑜伽士,敏感度将逐渐提升,因此会有一段极危险的过程,甚至可能陷入疯狂或死亡。
瑜伽修行者必须在上师的指导下接受拙火觉醒的秘密教诲,修行者一旦变成个中能手,意识的转化便以神秘的景象显现。他的身心必须经过一段非常危险的过程,在这段过程中,他自然会受到徒弟的护持,四周通常充满着神秘而又宁静的保护气氛。
克里希那穆提在奥哈伊经历这段过程时,尼亚和一位年轻的美国女孩罗莎琳·威廉斯都在场,兄弟俩事后分别写信给安妮·贝赞特报告这个事件。尼亚在信中很清楚地描述了哥哥所经历的痛苦。克里希那时而痛苦,时而昏迷,不断用泰卢固语呼叫母亲的名字,要母亲带他回到印度的树林。他一直抱怨木屋里的灰尘太多,并且要求尼亚和罗莎琳不要碰他的身体。当时克里希那的意识显然空了,在这份空性中,似乎有某种伟大的力量存在,最后克里希那走到屋外的一棵胡椒树下静坐。尼亚对整个事件的描述虽然受到通神学会术语的影响,仍然明显地表露了他对哥哥的深切关怀,以及整个事件带给他的焦虑和不知所措。
克里希那自己也写了一封信给贝赞特夫人,报告整个过程的来龙去脉:
8月17日,我感到后颈有股剧痛,只好把静坐的时间减少到十五分钟,结果痛苦并没有减轻,反而更糟。19日疼痛达到巅峰,我无法思考,也不能做任何事,周围的朋友强迫我上床睡觉。我几乎不省人事,但周遭发生的事我都能察觉。每天中午时分我才完全清醒。处在这种情况的头一天,我有了第一次不可思议的经验。我看到一个男人在那里修路,那个男人就是我,他手上拿的鹤嘴锄是我,他敲打的那块石头也是我,路旁的小草和他身边的大树也都是我,我几乎能和他一样地感觉和思考。连微风吹过树梢,吹过草上一只蚂蚁的感觉,我都能接收到。鸟儿、灰尘、噪音都是我的一部分。就在这时,有辆汽车停在不远的位置,我发现我也是那司机、引擎和轮胎。那辆车后来逐渐远去,我也逐渐脱离自己的身体。
我处在每一样东西里,而每一样东西也都在我身上,不论是有生命的或没有生命的,包括高山、小虫和所有能呼吸的东西在内。整天我都保持在这种大乐的状态,什么也吃不下。晚上六点左右,我的身体开始失去知觉,我进入了半昏迷状态。
第二天早晨(20日),情况几乎和头一天差不多,一整天我什么也没吃,我甚至不能忍受房里有太多人,我能以很奇怪的方式感受到他们,而他们的磁场令我神经紧张。当天晚上差不多六点左右,我觉得难受极了,我不希望任何人靠近我,或碰我的身体,我感到极为疲倦虚弱。在这种快要枯竭和六神无主的状态中,我忍不住哭了。我的头顶好像被许多小针刺穿一般,我突然觉得我躺的那张床脏死了!我根本无法在上面睡觉,接着我就发现自己已经坐在地板上了。尼亚和罗莎琳要我回到床上,我请求他们不要碰我,而且大叫床不干净。
这种情况持续了一阵以后,我迷迷糊糊走到阳台,精疲力竭地坐了下来,感觉稍微平静一些。我清醒以后,威灵顿先生(通神学会在美国的总干事)建议我到外面的胡椒树下静坐。我静坐了一会儿就逐渐感觉自己离开了身体,我透过树枝上的嫩叶看到自己的身体坐在下面,整个人是面向东方的。
我的身体在我的前方,我的头顶上方出现一颗明亮而清澈的星星,我似乎能感受到佛陀的磁场,也清楚地看到弥勒尊者和指导灵库特忽米。我感觉出奇地的快乐、平静和安详。我仍然能看到自己的身体飘浮在半空中,我觉得自己内在的祥和就像深不可测的湖心一般,而我的意念和情绪就像湖面的波纹,一点也无法干扰我灵魂的祥和。这股神秘的巨大力量,在我身边驻留了一会儿,不久便消失了。
我对所发生的一切感到极为快乐,我知道我永远也不会再回到旧有的状态,因为我已经尝到了生命的泉源。我的灵魂已经得到满足,我永远也不再饥渴,永远也不再回到黑暗中。我见到了神圣的治疗荣光,生命源头的真相已为我揭露,黑暗也已经被驱散。爱与其他所有的荣耀陶醉了我的心,我的心不再尘封。我终于尝到了喜悦的泉源和永恒之美,我完全陶醉在上帝的怀抱里。
往后的十天,克里希那的身体逐渐在恢复中。9月3日,他的脊椎有股特殊的感觉,他的意识再度离开身体,不久剧痛又开始了,当时有三个证人在场:尼亚、罗莎琳和威灵顿先生。尼亚把细节都记了下来,但是没有人了解这个事件的含义。1923年2月11日,尼亚亲手写了一张便条给贝赞特夫人,这张便条多年来一直摆在阿迪亚尔总部杂乱不堪的档案中,直到最近才被重新发现。尼亚写道:“我不知道该把这件事写成科学的程序,还是在寺庙中进行的神圣仪式,事情总在每晚六点左右开始,很有规律地在八点结束,中间有几天曾经延迟到九点。”
每天晚上,克里希那都在胡椒树下静坐。9月3日,他结束静坐以后,就在半昏迷中进入房间倒在床上,接着他开始呻吟,抱怨燥热难挨,他打了一个冷颤,又扑倒在床上。他重新恢复知觉以后,完全不记得刚才所发生的事,只是有点不舒服而已。第二天晚上同样的症状再度出现。9月5日,他到好莱坞去看一出有关基督的舞台剧,他很久以前就安排好了这件事,所以不愿悔约。他事后告诉尼亚,看戏时他发现自己正在逐渐失去知觉,费了好大气力才醒过来。6日的晚上他回到奥哈伊,那天刚好是月圆之日。
7日晚上的月亮仍然十分皎洁,尼亚作了下面这段札记:
克里希那从树林走向我们,我们看得很清楚。他穿着印度服的样子看起来像幽灵一般。他艰难地的走着,几乎快要支持不住了。他走到我们面前,眼神看起来像个死人,我们站在他的面前,他却视而不见。起初他还能条理分明地说些话,不久就不省人事了。他那颠颠倒倒的样子,看起来十分危险,罗莎琳和威灵顿冲向前去扶他,他立刻大叫:“拜托你们不要碰我!拜托!我好痛。”然后就回房躺到床上。我们把所有的窗帘都拉上,让房间保持黑暗,但是月光仍然十分明亮。罗莎琳在一旁静候,不一会儿他突然站起来,好像在对一个隐形人说话似的:“什么?好!我马上来。”说完以后,他就开始往外走。罗莎琳想要阻止他,他却回答说:“我很好,请不要碰我,我真的很好。”
他的声音听起来虽然有点不耐烦,但是还算正常,罗莎琳便准许他一个人往外走。走了没两步,他整个人突然面朝下扑倒下去。事后他完全不记得自己怎么摔倒的,也不记得倒在什么地点。
玄关的地方有一张长板凳,板凳下面有许多突出的木箱,他完全没有察觉这些,撞东撞西地快要昏倒的样子。有时他会突然从床上坐起,喃喃自语一阵之后,不是向前就是向后倒下,有时甚至摔在地板上。他每分每秒都需要别人的照顾,但是他一发觉周围有人监护他,就不耐烦地说:“我很好,请相信我,我很好。”即使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都是含糊不清的。他不断呻吟并且翻来覆去,语无伦次地抱怨着脊椎的疼痛。
任何一点声响,即使是低声交谈都会干扰他,他哀求周围的伙伴不要讨论他,让他独处,因为他们的声音令他觉得极为痛苦。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晚上八点。将近八点,他就变得较为平静安详,逐渐恢复了正常。
9月10日晚上,克里希那开始呼叫母亲的名字,他叫了几声以后对尼亚说:“你看到她没有?”当他完全清醒以后,他告诉尼亚:“母亲的脸孔刚才出现在罗莎琳的脸上,两张脸后来合为一体了。”这时他早年的回忆再度浮现,好像重新经历了一次童年往事。
尼亚和威灵顿不久就明白,克里希那正处在非常危险的拙火觉醒时的意识转化过程。他们感觉周围的氛围充满着一种无形的磁力,他们觉得自己好像正在守护寺庙中进行的神圣仪式。克里希那身边的人,时常觉得无形中有一位神明在坐镇一切,虽然他们看不到也无法证明他的存在。克里希那却时常和这位既像朋友又像老师的无形存有交谈。克里希那不能忍受任何光线和声响,别人一碰他的身体他就大叫,他也不能忍受周围有太多的人。他的身体和心智的敏感度,好像调到了最高。他身体上的某一点会突然剧痛,这时他就把周围的人推向一旁,抱怨屋里太热。
9月18日又有了新的转变,克里希那的痛苦更加强烈,也更加烦躁不安。他有时视而不见、颤抖和呻吟,有时又向虚空中的无形存有发问,当他太痛苦的时候便大叫:“拜托!哦!拜托给我一点时间。”然后开始呼喊母亲的名字。
9月18日晚上的八点十分,他坐在床上非常清醒地和大家交谈,几分钟以后就不省人事了。他的身体好像有一个巨大的伤口一般又开始阵痛,这次痛点转到了身体的另一个部位。他痛得忍不住尖叫。尼亚听到躺在黑暗中的克里希那不断地大叫,不断地喃喃自语,甚至哀求那存有延缓这整个过程。周围的人不久就学会辨认克里希那发出的两种声音,一种是他四大假合的身体发出的声音,另一种则是克里希那发出的声音。晚上九点十五分以后,克里希那又恢复了知觉。整个转化过程似乎是计算好的,每天晚上只进行到某种程度,如果开始的时候受到干扰,结束的时候就会得到补足。往后的十五个夜晚,每当他正在受苦时,他会突然问周围的人几点钟了,答案永远是七点三十分。
神志清醒之后,痛苦自然一扫而空。尼亚和罗莎琳通常会告诉他刚才所发生的事,而他就像在听另一个人的故事一样。
9月19日,状况比以前恶化,转化过程在他神志不清时毫无预警地开始了。痛苦愈来愈烈,痛到克里希那突然站起来向外狂奔,周围的人唯恐他会扑倒在石头上,极力想抓住他,他也极力想挣脱。过了一会儿,他忍不住哭了起来,他狂喊着:“哦!母亲!你为什么要生我?难道你生我就是为了要我承受这一切吗?”根据尼亚的形容,他的眼睛看起来神志不清,充满着血丝,除了母亲之外,谁也认不出了。他抱怨有一团火在体内燃烧,他因为哭得太厉害,所以不停地咳嗽并发出咯咯声,但是这种情况很快就停止了。痛苦实在难以忍受了,他会突然站起来往外跑,我们就绕着他追。有三次他都想逃脱,他一看到我们在他周围,便稍微安静一点。有时他会非常肯定地说:“我还能承受更多的痛苦,不要管我的身体,我只是无法停止哭泣而已。”
9月20日的晚上,痛苦更剧烈了,克里希那有五次到六次都想逃跑,他的身体有时还扭成怪异而危险的姿势。尼亚在札记中写道:“有一次克里希那正在呜咽,突然他把头钻进两膝之间倒转过来,差点把颈子扭断,还好罗莎琳正在旁边,赶紧帮他转向一侧。不久,他突然变得完全死寂,连心跳几乎都停止了。”
第二天,罗莎琳有事必须离开数日,当她不在的期间,转化过程突然慢了下来,但是克里希那仍然抱怨左边脊椎下方有股怪异的疼痛感。
有一次,克里希那看起来非常烦躁,他觉得有人在屋子里窥视他,他坚持走到矮墙边,然后大声地说:“走开!你来这里干什么?走!我怎么知道你要到哪里去?你到山后去算了,现在你得马上离开这里。”接着他回到屋里躺下,不久又开始大叫:“克里希那,你快点回来!”他一直不停地叫着克里希那,直到失去知觉为止。这是他第一次叫自己的名字,当天夜里,他后颈的疼痛更严重了。
罗莎琳回来之后,他的疼痛更加剧烈,他抱怨脊椎发热,无法承受太亮的光线,连日出时的光线都受不了。在整个过程里,他又再度站起来,向虚空中的隐形人抗议,他看起来非常愤怒,那个隐形人从此就不见了。当光线实在太强时,他们只好把他领进屋里。有一天傍晚快要接近五点时,屋里的氛围突然改变了,变得非常安静而祥和。周遭的人似乎觉得有一位伟大的存有在现场指挥一切,尼亚形容当时就像一个巨大的发电机在运作,几个小时以后整个屋子都震动了起来。
到了10月2日左右,新的情况又开始了,剧痛转移到克里希那的脸和眼睛,他感觉那股无形的力量正在对他的眼睛下工夫,他说:“母亲!请你摸摸我的脸。它还在那儿吗?”不久,他说:“母亲!我的眼珠不见了,你摸摸看,它真的不见了!”他一边说一边开始呜咽、呻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晚上八点。九点以后,他开始全身颤抖,几乎不能呼吸。
当时的情况给人一种感觉,好像真正的克里希那不愿意回到他的身体,因为实在太痛苦了。根据尼亚的形容,每次克里希那快要清醒时,全身就开始不停地颤抖。
13日那天,他问罗莎琳:“母亲!你能不能照顾我,我要到很远的地方去。”说完以后就不省人事了。
过了一阵,当他清醒以后,第一件事就是问罗莎琳,“克里希那跑到哪里去了?”他说,“我把一切交给你处理,而你却不知道克里希那跑到哪里去了!”接着便开始低声哭泣。他坚持要等克里希那回来之后才睡觉,一个半小时以后他才入睡。
有一天早上,他们都在威灵顿家,克里希那的神识突然离开了身体,他早先告诉过罗莎琳他要到很远的地方去,要她好好照顾他的身体。两个小时以后他才开始说话。他看到罗莎琳的双手,很惊讶地质问着:“母亲!你的皮肤怎么是白的?”接着又说:“你变得年轻多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又说:“母亲,克里希那就要进来了,看!他就站在那里。”罗莎琳询问他克里希那的长相,他说:“他是一个高大俊美的男人,非常庄严,我对他有点敬畏。”然后他说:“母亲!难道你不认识他吗?他是你的儿子,他可认识你咧!”
10月4日的夜晚,克里希那比平常更痛苦,剧痛集中在他的脸庞和眼睛,他不停地说:“哦!请对我慈悲一点。”然后又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对我已经够慈悲了。”
事后克里希那告诉尼亚,那股无形的力量当时正在清理他的双眼,使他有能力看到他,他说:“我当时就像被绑在沙漠上,眼皮被割掉一样地面对着烈日。”
当天夜里,尼亚突然发现克里希那在床上静坐,他感觉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充满着整栋房子,所有的痛苦都一扫而空。尼亚事后在信中写道:“克里希那没有看到他的脸,只看到他充满着光的身体。”
第二天早上,克里希那的情绪非常难以控制,他昏昏沉沉地坚持要出去,他们不得不制止他。事后他解释,当时脊椎上有一股可怕的炽热感,他想跑到峡谷的溪流里解热。
过了一段时间,周围的人再度感觉到那个伟大的存有。“克里希那的眼睛看起来出奇地明亮,连样子都变了。他走进来时,屋里的氛围变得十分奇妙,克里希那脸上带着至乐的表情。”他告诉尼亚、罗莎琳和威灵顿,准备当天夜里迎接一位伟大的访客,他要求他们在他房里摆设一张佛祖的肖像。
克里希那结束静坐进入房间,他告诉他们那位伟大的存有在他静坐结束后就离开了。
~~~~~~~~
当天晚上情况十分恐怖,似乎是克里希那最痛苦的一夜。第二天晚上情况更糟,尼亚认为那是因为头一天晚上的虚弱造成的。痛苦没有开始以前,他们听到他和指挥这一切的指导灵交谈,指导灵要他不许告诉任何人这里发生的事,他答应了。指导灵告诉他那位访客在晚上八点十五分会再来。克里希那说:“他如果八点十五分会再来的话,就让我们快点开始吧!”在疼痛尚未开始之前他突然站了起来,他们听到他重重地摔在地上,他们又听到他充满歉意地说:“对不起,我摔倒了,我知道我不该摔倒的。”当天晚上他开始更加注意自己的身体。指导灵告诉他一定不能动来动去,他答应了,他一次又一次地保证:“我不动!我不动!我答应过我绝对不会动的。”他把手指紧紧交叉在背后,平躺下来,静静挨过再度出现的疼痛。
当天晚上他发现自己开始呼吸困难,他喘着气,几乎快要窒息了。当他实在无法忍受疼痛也无法呼吸时,便昏了过去。他昏过去三次,第一次昏倒时,他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只听到他哽咽的声音,在一阵长长的喘息之后就死寂无声了。他们叫他,他也不回答,他们只好在漆黑的屋子里摸索,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他躺在哪里。后来终于找到了他,他躺在床上,双手压在背后,像座石像一般。
就这样他昏过去三次,每一次醒来时,都满怀歉意地告诉指导灵他已经尽力控制自己,但是实在忍不住。有的时候,他们给他一点喘息的空当,痛苦便停歇一阵,这时克里希那就和那位无形的主使者开始谈笑风生,好像整件事不过是场玩笑罢了。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小时零十五分。七点四十五分,克里希那开始呼唤母亲的名字,罗莎琳静悄悄地走进屋去,他突然变得非常紧张,大叫:“是谁!是谁!”她走近时,他突然昏倒。处在最敏感的状态中,任何人走进来都会令他烦乱。她陪在他身边一段时间,不久他就要求她出去,因为他快要进来了。罗莎琳和尼亚走到外边的长廊,让克里希那一个人在屋里静坐,他们像往常一样,又感觉到那位伟大的存有。
尼亚和罗莎琳再度回到屋内时,克里希那正在和一群他们看不见的人说话,转化过程显然已经成功,那些人似乎在恭喜他,屋子里好像有非常多的访客想和克里希那一起庆祝这一次的成就,他似乎有点穷于应付。他们听到他说:“我实在没什么好恭喜的,你们大家都经过这个过程的。”
不久,他们显然全都离开了房间,因为克里希那长叹一声之后便躺在床上,许久都动弹不得。然后他又开始说话:“母亲,一切都大不相同了,经过这次事件以后,我们的人生再也不会和从前一样了。”接着他又说:“我已经见到他了,母亲,现在一切都无关紧要了。”他一再重复这些话,而他们也都觉得从此以后会大不相同了。
尼亚入睡之前,克里希那又开始和一个他看不见的人说话,从克里希那的话中,他们知道这个人显然是指导灵左瓦库派来守护克里希那身体的,克里希那一直向他道歉。当天夜里这是唯一引人注意的事。他不论清醒与否都同样多礼而体恤。此后的六七个晚上,那个男人固定前来守护,克里希那告诉他们:“我已经看到他了,一切都无关紧要了。”
~~~~~~~~
这段期间他的身体一直很虚弱,时常不省人事。
10月6日那天,痛苦开始转移到头顶,他的头顶好像被切开一样,那是无法形容的痛苦。有一次他大叫:“请把它合起来!请把它合起来!”他痛苦地大叫,他们似乎仍然在逐渐开启他的头顶,当他实在不能忍受疼痛时,就大叫一声昏倒过去。四十分钟以后,他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后来慢慢清醒过来,和他的伙伴说话,他们发现他的声音变成了四岁的小孩。他似乎又回溯到早期的童年,甚至重新目睹了母亲生产时的情况,他为此痛苦不已,一直不停地大叫:“哦……可怜的母亲,可怜的母亲,你真是一位伟大的母亲。”接着又回到他和尼亚小时候得疟疾的景象。
最后一幕是他母亲去世时的景象,当时他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看到医生给母亲吃药,他哀求她不要吃下去:“母亲,你不要吃,千万不要吃!这不是什么好东西,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这个医生什么也不懂,他居心不良……母亲,你千万不要吃!”过了一会儿,他的声音变得非常恐怖,他说:“母亲,你为什么那么安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父亲为什么要遮住他的脸?回答我!母亲你快回答我啊!”这种小孩的哭声一直持续着,直到克里希那穆提回到自己的体内为止。当天晚上他入睡之后,那个无形的存有又来守护他。
第二天夜里,据尼亚描述,“他们好像正在他的头顶开刀”。他痛得大叫,昏过去八次。“他哀求他们慢慢地开,好让他一点一点的适应”。
不久他又变成了小孩儿,周围的人都可以感觉到他不想上学。“母亲,我今天不必上学吧?我身体非常不舒服。”过了一会儿,他说:“母亲,让我待在家里,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不久他又说:“母亲,你知道吗?你把饼干盒子藏起来不让我们拿到,可是我已经从那个盒子里偷了饼干,偷了很久了。”罗莎琳忍不住笑了出来。他很伤心地说:“母亲,你老是喜欢笑我,你为什么笑我?”
过了一会儿,他说了一大堆有关蛇、小狗以及乞丐的事,接着说起家里那个做火供的房间,他说:“我看到一个女的盘坐在鹿皮上。”尼亚好像记得那张照片是贝赞特夫人的肖像,克里希那穆提却完全不认得她了。
不久,他似乎很容易就能够出神,而回到身体时也不再颤抖了。那天夜里晚一点的时候,指导灵似乎把他的顶轮打开了,那个隐形人再度来到他身边守护。
克里希那的话一天比一天少。夜里仍然昏迷不醒,但是醒来的速度比从前快多了,精力也比从前充沛许多。
他有时仍回溯到儿童时代。10月18日,阵痛愈来愈强。他们又有幸见到那位伟大的存有。19日那天,有件奇怪的事发生了。他静坐完回到屋里,开始一遍遍地叫着克里希那,他高喊着:“克里希那,拜托你不要离开我,克里希那。”
事后他告诉尼亚以及罗莎琳:“要小心照顾克里希那,永远不要突然叫醒他,也不要吓到他,这是非常危险的,出任何差错,事情都会搞砸。”转化过程从此逐渐减缓。到了1923年11月才止息下来。
这个连赖德拜特和贝赞特夫人都无法解释的转化过程,又间歇地持续了好几个月。他的身体仍然剧痛、扭曲,有时甚至倒到地板上。克里希那时常要求他的弟弟和其他人离开他的房间,而他们也不忍看到他受苦。
1924年,克里希那和一些朋友出国旅行,转化过程仍然持续着,痛苦接近尾声时,他看见了佛祖、弥勒尊者和其他的指导灵。3月24日,他们从意大利的佩尔几内回到奥哈伊,尼亚在极度困惑中写信给安妮·贝赞特:
克里希那的转化过程有着明显的进展,前几天某个晚上,在我们意料之中过程又开始了。我们突然感觉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巨大能量,克里希那见到了尊者和指导灵,我们大家也都有强烈的敬畏感。
克里希那事后告诉我们,当时有股能量像往常一样从脊椎的底部向上升达他的后颈,接着分成两路,一条往左,一条往右,然后交会在前额的中央。当它们交会时,前额发出了一股火焰。我们没有人懂得这件事的含义,那股能量非常强烈,使得当夜的转化过程进入了明确的阶段,我猜想他的第三眼已经完全打开了。
除了见到尊者之外,其他的描述都是典型的拙火觉醒时的情况。
~~~~~~~~
1925年11月上旬,贝赞特夫人、克里希那吉、拉嘉戈帕尔、罗莎琳、卫奇伍德、西瓦·罗、鲁克米妮、乔治·阿伦戴尔,同赴印度的阿迪亚尔,参加通神学会的五十周年庆,当时克对于指导灵预言尼亚不会死这件事,仍然充满信心。1925年的年初,尼亚已经病重,2月10日那天克写了一封信给贝赞特夫人,描述他如何探访净光兄弟,并且请求它们延长尼亚的寿命:
我记得我到了指导灵的家,请求他们庇佑尼亚继续活下去。指导灵要我去找弥勒尊者,我到了尊者的家,觉得这件事好像和尊者无关。他要我去找马哈可汗,我到了马哈可汗家,他正坐在椅子上,看起来非常庄严而善解人意,表情凝重而又慈祥地看着我。我实在无法形容他给我的非凡印象,我告诉他我愿意牺牲一切来换取尼亚的性命,他听完我的话,很坚定地回答我:“他会好起来的。”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所有的焦虑一扫而空。
至于我自己的准备工作,我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决定,无论如何我将全力以赴。这一阵子我觉得非常疲倦而虚弱,大概都是必经过程。我的母亲,谢天谢地,你终于要回来了。
全心全意爱你的克里希那穆提
这一次和指导灵的接触,使得克深信他们将延长尼亚的性命。如果我们暂停下来,仔细检查克里希那吉和指导灵的接触,无论库特忽米、马哈可汗、弥勒尊者或佛陀,这些影像全是在睡眠状态产生的。这种情形在他小的时候就有了,他因为接受了赖德拜特灌输给他的念相以及各种神的肖像,于是他看到的指导灵自然和通神学会秘授部门的神像完全相符。他早期写给贝赞特夫人的信中所描述的库特忽米,以及在奥哈伊拙火觉醒的过程中见到的指导灵,都是在暗示下见到的幻象。拙火觉醒以后,他便逐渐从这些幻象中挣脱了。
小的时候,清醒的状态和睡眠的状态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差别,无论影像、梦境或念相,对他而言都是同一回事。年长以后他曾经明白地表示,所有的影像和幻象无论多么奇妙,都不过是心念的投射而已。后来他接到尼亚的死讯,这股爆发性的巨大伤痛,突然使他不得不面对事实,从此以后他就不再谈论见到指导灵的事了。
就在尼亚死前不久,大伙儿坐船回印度时,阿伦戴尔开始声称自己接到马哈可汗的启示,他说除非克接受他所选出来的门徒,否则尼亚必死无疑。克里希那穆提还是拒绝了他的要求。
当船通过苏伊士运河时,克里希那穆提接到一份尼亚染上感冒的电报,第二天尼亚又拍了一份电报说:“感冒越来越严重,请为我祈祷。”当时克仍然信心十足地对西瓦·罗说,如果他的弟弟命中注定要死,指导灵就绝不会让他离开奥哈伊。11月13日那天,在狂风暴雨中,他们接到了尼亚的死讯。
西瓦·罗和克睡在同一间舱室内,他把当时的印象写了下来:
贝赞特夫人要我带她到克的舱室,她单独进去和他谈话。尼亚的死讯让他的心完全碎了,可能还不只如此,我觉得他整个的人生哲学,包括赖德拜特和贝赞特夫人为他设计的未来愿景,也全都毁灭了。清醒时他沉默无语,睡梦中他则哭喊着尼亚的名字。日子一天一天地消逝,他似乎也完全改观了。他强忍着痛苦,独自面对一个不再有尼亚的人生。
在陌生的国度里,克里希那和尼亚长久以来一直分担着彼此的孤独,他们一同欢笑,一同旅行,一同设计未来的工作与人生。尼亚死后,克里希那吉写了下面这段话:“旧梦已死,新梦重生,全然不同的视野与意识开始展现。我曾经哭过,但是我不希望看到别人哭;如果他们哭了,我能够感同身受。尼亚和我已经融为一体,我知道我们将永不分离,我们将共同为人类服务。”
当贝赞特夫人和克抵达阿迪亚尔时,克已经从痛苦中走了出来。他看起来极为安详,整个人容光焕发,所有的情绪一扫而空。他过去臣服于指导灵的信仰,此刻有了***性的转变。从此他很少再提起看到指导灵这回事,多年以后在别人的要求之下,他不太情愿地谈起在船上发生的事。他认为,当时那份强烈的伤痛,也许引爆了无法言传的悟性,长久以来一直在臣服中蛰伏的智慧,突然在痛苦的一刹那觉醒。
更新于:2023-09-16 14:1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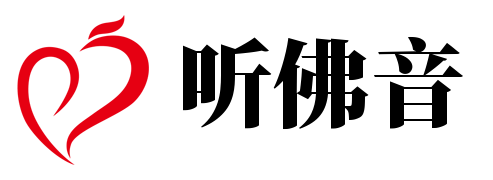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