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云法师:弘法利生
我童年是在一个偶然的因缘下出家,当时我是栖霞律学院里年龄最小的一个。有一天,我读到这么一句话:“僧伽应以弘法为家务,利生为事业。”
少不更事的我,这时才知道出家人原来背负著如此神圣的使命,一时之间恍然大悟:我学佛修道还是嫌太迟了!如果我早一点来此,就可以养深积厚,早一点荷担如来家业。此后,每当早课讽诵〈楞严咒〉,唱到“愿将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时,我都在心中发愿:“我将来一定要将全部的身心奉献在弘法利生上。”
时至今日,我乐说不怠,也建立了各种佛教事业。在佛陀的加被下,我一生所作所为无一不是为了达到“弘法利生”这个愿心,而力行实践。虽说是“愿不虚发”,但是早期弘法时所经历的艰辛困苦,却也鲜为人知。
五○年代的台湾不但物质生活不丰,更是一块缺乏正信佛法的沙漠,我立志要遍洒甘露法水于台湾各地,润泽群生。于是,我带著一批有志青年,以拓荒者的精神,四处弘法布教。举凡邻里、乡镇、街市、陋巷、庙口、戏院、海边、山地,皆有我们行脚的足迹。每到一处,我们亲自动手拉电线、装灯泡、安麦克风、排椅凳、张贴海报、招呼听众……,然后才登台讲演。尽管刚开始时,闻法者很少,我却从不气馁,因为只要有人愿意来听讲,就有人能受到法益。只是往往时间到了,台下一个人也没有,我照常开讲,过了很久,听众才姗姗来迟。后来,大家养成了守时的习惯,听众也越来越多,这时又出现了走动移位的现象,我总是以缄默来教育信众,这种对治方法不久便产生成效。
为了购置布教设备,我将平日微薄的红包供养花用殆尽,日中仅以一块面包果腹是常有的事。凡是不远的地方,我们便以单车代步,在风和日丽的时候,迎著夕阳,沐著晚风,倒也别有一番乐趣。不过有时碰上梅雨季节,或是寒流来袭,尤其是大台风天,在凄风苦雨的肆虐下跋山涉水,实在是备尝辛苦。然而看到听众逐渐由少而多,冒著风雨,闻法虔诚的态度,在感动之余,也忘了饥寒冻馁的难受。路程遥远的地方,则搭乘火车,沿途田园风光旖旎,令人陶醉其中。只是那时火车班次不多,我们经常为了赶火车而行色匆匆。后来,宜兰线火车站的站长被我们的弘法热忱所感动,往往等我们全都到齐了,才下令开车。
最令我难忘的是:每当布教圆满结束时,在信徒的欢送下,踏上归程,我们盛载满怀的温馨,走过阡陌田野,穿越树林山洞,以充满法喜的歌声,划破万籁俱寂的夜空,我们的心就像当头的皓月一般明净,我们的身有如掠过的微风一般轻盈。我们间或交换弘法心得,谈起化导顽民的富楼那,一股圣洁的使命感冉冉升起;说到为法丧身的目犍连时,又燃起了悲壮的情怀……,我们誓言以高僧大德为榜样,以续佛慧命为己志。一天,我福至心灵,将这种景象与心情描绘在诗篇上,请人谱曲,这就是后来我们在弘法归途中常常高吟的“弘法者之歌”。
最令我安慰的是:当年跟随我忍饿受冻的年轻人在参与活动中茁壮成长,如今都有了美好的前途。而当时的辛苦播种,如今在各地都已绽开菩提花果,则是我一生中最丰硕的收获。
多年来,只要有地方需要佛法,有人邀请我去,再远再忙,即使牺牲吃饭、睡觉的时间,我都欣然答应。记得有一次,到南投鱼池乡布教,夜宿农舍,因为卧处与尿桶为伍,臭气难闻,无法入眠,只得央求同行的煮云法师为我说故事。后来,为了不负他的辛劳,我将这则故事写成了《玉琳国师》,风行一时,也算是弘法外的一桩趣谈美事。
那时,我虽然住在宜兰,却经常要到高雄讲经,每次坐火车,转公车,就要周折上一整天的时间,平日还得节衣缩食,凑足车资。有一回,查票员来验票,火车票却遍寻不获,身上又没有半毛钱,只得掏出一支新买还没用过的钢笔充当补票之款。我这样南北奔波达十余年之久,心中乐此不疲,我不畏舟车之苦,只怕没有人知道佛法的好处。直至今日,我已走遍了整个台湾,行迹还远及离岛,并且直迈国际州郡。曾听到有人调侃我,说我已经退位了,犹仍四处云游弘法,野心实在太大!其实,此言差矣!我虽然卸任住持,但是并没有不做“和尚”,出家人本来就应该有著“弘扬佛法遍天下,普渡众生满人间”的慈悲心肠,这不是“野心”,而是一种难行能行的“愿心”啊!
如今,我到各地说法,不必刻意宣传,听众自然蜂涌而至。过去,我唯恐人不来,现在却以人多为苦,因为我不忍心看到人们因为一票难求,而甘冒风吹日晒,早早伫立在门外,苦苦守候进场;我也不忍心目睹观众在场内挤得连站的位子都没有;我更不忍心看到那些有心闻法的善男信女因为会场容纳不下,或因稍微地迟到而被阻挡于门外。我曾一再请求有关主管通融,无奈碍于规定,而无法如愿。一九九二年,我到马来西亚东姑讲堂开示,场内爆满,有一千多名听众没有位置可坐,场外还有两千多人不得其门而入,有的拍门叫嚷:“让我们进去!难道我们的师父来此,都不让我们见一眼吗?”有的甚至走太平梯,以旁门左道的方式出奇致胜,进入会场。那种闻法的热忱直叫人感动难忘!
出家人忧道不忧贫,佛法上的安乐足以弥补生活上的困乏,人为的阻挠才是弘法上最大的考验。
回忆我在宜兰初次讲经时,警察不准我公开说法,禁止我播放佛教幻灯片,他们所持的理由是:“你没有向有关单位呈报申请。”在雷音寺弘法时,也有一些外道居民在殿外喧嚣干扰;广播电台的佛学讲座录制好了,电视台的佛教节目制作完成了,却因为对方的负责人声称“限于目前当局政策,不希望富有宗教色彩的节目播出”,而临时遭到封杀的厄运;怀著满腔热情,想要到军中、监狱为三军将士及受刑男女作得度因缘,却被冷冷地拒绝,问他们:“为什么天主教的神父、修女以及耶稣教的牧师可以到这里传教,而佛教僧尼却被摒于门外?”他们答道:“因为出家人不宜进入说法。”再加追问:“同是布教师,为何有如此差别待遇”时,得到的只是更加冷漠的表情;台北师范学院(即今师大)请我讲演,海报都已经张贴出去,也无缘无故地被取消作罢;到公家机关礼堂说法,供奉佛像受到排斥……。我并不因此而自怜自艾,相反地,我愈挫愈勇,我据理力争,所谓:“为大事也,何惜生命!”
佛陀在因地修行时,曾被歌利王割截身体而毫无怨尤;地藏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我要效法诸佛菩萨为法忘躯的精神”我在心中不断自勉。
心中的悲愤尚未平抚,治安单位又前来调查,因为中央情报局接到黑函密告,说我:“言论可疑,恐有通敌之嫌。”我并不为此而愤世嫉俗,相反地,我学会了以平常心来应付这些纷至沓来的障碍与诽谤,“我要为佛教的千秋大业而奋斗不息,我要为万亿众生的慧命而努力不懈!”我如是自许。
果然,打击非难成了我的逆增上缘,我的坚持理想有了代价:如今各地警政***亲自邀我至各个警察单位演说佛法;警官学校、警专学校、三军官校、宪兵学校等,我都曾作过佛学讲座。有一次,宜兰县议员在议会上讨论到当地寺庙殿宇修建得金碧辉煌时,都一致归功于我在当地二十年的弘法贡献;甚至我现在要著手创设大学,宜兰县当地政府也主动争取;广播电台、电视台争相请我录制节目,并且给予酬谢;军中、监狱不断寄发公文,向我请法;大专院校的讲演多得不计其数;情报治安单位也一再要求我能广开法筵,以端正社会风气;各县市长、各级***,甚至参谋总长还颁发奖牌、奖状,以资鼓励;在国父纪念馆、中正文化中心的国家殿堂开大座,也极受礼遇配合。
我一生弘法无数,感到最难的是如何契理契机。最初,往往为了一篇讲稿,日夜揣摩听众心理;常常为了一句名相,反覆思惟其中深意,为的是希望大家都能听懂受用,并且能将佛法妙谛运用在生活上,以作为现实人生的指南。
我从不卖弄玄虚,只是一心一意在宣扬佛法的真理,使佛法与世间的生活能够相印证。我经常思虑如何发挥佛教的时代性与前瞻性的功能,期能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为了契合信众的需求,使佛法能普及于社会各个阶层,我不但组织念佛会,还设立青年歌咏队、儿童星期学校、妇女法座会、金刚禅座会。为了助长说法效果,我利用板书、投影机、各种视听设备,乃至在大座讲经时,精心设计献供仪式,穿插各种佛教艺术节目。为了让社会人士重视佛教,我率先举办佛诞花车游行,并且多次举行环岛布教活动……。凡此种种创举都在当时引起不少保守人士的非议责难,我并不因此而裹足不前,相反地,我大力推动,我以为:只要佛法兴隆,何须计较个人荣辱得失?
我的择善固执终于有了明证:环顾今日的佛教界,当年反对我的同道都不约而同地接受了人间佛教、生活佛教的理念;各地的道场寺院也都不断地以各种活动来凝聚信众的力量;更有不少青年在这种因缘下随我学佛,现在都成了佛光山重要的职事干部。
我当初的用心良苦,斟酌思虑,促成了我对于佛法的融会贯通,更是我始料未及的收获。我走入群众,学会了观机逗教,士、农、工、商,老、弱、妇、孺,鳏、寡、孤、独,都是我说法的对象。我也曾远走中国内地,深入泰北边区,抵达香港越侨船民营房,为苦难同胞作得度因缘。
现在,我每天的行程被弘法的邀约排得满满的,我日日奔波忙碌,以车厢、飞机作为我的卧室和书房,我赶场弘法,由此地到彼地,由此国到彼国,甚至由此洲到彼洲,席不暇暖。我经常和衣而卧,一觉醒来,蒙眬之中,往往一时弄不清楚自己身在何处。我不以此为苦为累,自忖比起佛陀年高八十,犹不辞辛劳,在印度各地行脚弘化,我这一点苦实在不算什么。尤其,当我看到许多人在台下会意点头,甚至抚掌微笑,一切的劳顿全都化为无比的愿力;当我看见许多人因为听了我的讲演而皈依三宝时,心中更是为他们的新生而感到庆喜!
我曾经在火车上,遇见一位不认识的青年让位予我,他悄悄地对我说:“师父!我是您在某某监狱弘法时的皈依弟子。”我蒙受过不少礼遇招待,上自政府***,下至社会大众,但这一次令我最为终生难忘。我也曾收到一份二百元的红包,上面写著:“供养师父:因听您讲演而改邪归正的弟子某某顶礼。”数目虽然微薄,意义却是深远重大。每每一场大型讲座后,感谢的信函即如雪片般飞来,其中,有失和的夫妻因此而破镜重圆者,有吵架的朋友因此而握手言欢者,有落第的考生因此而萌生希望者,有失业的青年因此而力图上进者,更有人因此而断除自杀念头……。来鸿中,赞美的诗词也不少,虽不尽然辞畅意顺,然而诚意却是十分感人。在海内外收到的纪念品,更是多得无法整理,还好我有喜舍结缘的性格,否则就是建一个大仓库,也无法全部容纳。
为了度众之需,三轮车、脚踏车、摩托车、木筏、竹排、轮船、汽艇、军舰、战车,乃至潜水艇、直升机,也都成了我的交通工具。虽是海陆空航道各异,然而承蒙三宝加被,法界任我遨游,岂不妙哉!
我不但自己乐于说法,也极力兴学,培养弘法人才。四十年来的度众生涯中,每得到一份供养,总是先用来建讲堂,盖教室;每领到一些稿费,也都悉数购买佛书典籍给青年学子阅读参考。我涓滴归公,从未想将丝毫用在自己身上。刚兴建佛光山时,徒众建议我买轿车代步,以便至各处讲说,我却买了一部巴士普利大众;目前我在世界各地讲演、皈依所收到的红包,也都捐献给当地的佛寺,作为发展道场之用。直到最近,念及佛光山建设佛教事业所费不赀,我才将外来出版厂商给我的版权收入,挪为自己平日的生活开销及车马费用,以减少常住的负担。
佛教之所以能流传千古,广被四海,文字般若的传递,功不可没。有识于此,我于来台之初,即致力于编辑杂志、撰文出书的文化事业。一九五九年,在三重埔设立佛教文化服务处,印行佛经。当时的经济十分拮据,编印人才也寥寥无几,但凭一股度众的热忱,我度过了捉襟见肘的窘困日子。记得有一次,我将编好的《人生杂志》连夜送到印刷厂,半夜醒来,饥肠辘辘,才想起自己一整天还没吃饭呢!又因为没有钱买稿纸,我常常拿别人丢弃的纸张背面做为涂鸦之用。直到现在,我依然是在年年亏损的情况下,兴办杂志、图书等文化事业,但我从无怨言,因为我深知:佛教的文化度众功能无远弗届,非金钱财富所能比拟。
此外,我还创设云水医院、老人精舍、育幼院、冬令救济等慈善事业,将佛教的爱心广泽于贫苦无依的老弱残疾。我曾多次发起中国大陆以及世界各地的救灾运动,而佛光山的创建,更带动了当地经济建设的繁荣,其本身就是一项利济众生的庞大事业,只是在这些方面,我甚少著意宣传。千百年来,佛寺道场在福国利民的工作上,何尝不是有多方面的贡献吗?
及至今日,我每至一处,只要见到一块空地,亟思如何来兴建寺院讲堂?只要认识一个人,总是尽力将他吸收作为佛教的一分子;只要看到一件好事,就迫不及待地广为宣传。这一切只是希望能将佛教的欢喜散播给一切众生。
过去常听到一些人说我:“好可惜哟!这么年轻就出家了。”对于这些言论,我深深不以为然。弃俗出家,弘法利生,是在做经世济民的伟大事业,怎么说可惜呢?我不但此生此世以出家为荣,我更发愿生生世世都要学习佛陀示教利喜的精神,来此娑婆,做一名“以弘法为家务,以利生为事业”的和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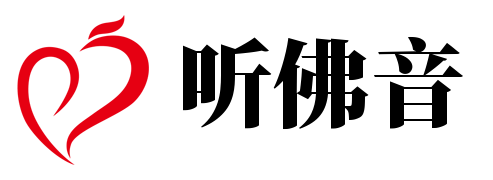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