槿花夜宴
槿花夜宴
在我很小的时候,有怪人之称的祖父就去世了。因为生前研究民俗学的关系,在别人看来祖父总有许多奇怪的规矩:比如让我和小我一个月的堂弟在七岁以前做一样的打扮,留长发,穿几乎不会有人穿的唐装;比如只允许我和堂弟以他取的乳名彼此称呼我的是火翼,堂弟的叫作冰鳍。
说起来是有点怪
我家世居古城香川,从未离开过旧城区的老宅。从小包围着我的就是那片冰冻在时间之中的白墙青瓦,仿佛被看不见的力量守护着一样,城市的喧嚣进不了曲曲折折的深巷。神秘的风俗和家常琐事早已融为一体,成为人们的生存方式,对于那些不可思议的事物,我不知道大家是习以为常还是根本就没有察觉。就在这一片不起眼的奇迹国土里,我和冰鳍度过了整个童年。
有些事,至今我们也弄不明白究竟真的发生过,还是根本就是个幻觉
我记得一个岁末的午后,临近年关家里似乎很忙的样子,没有人发现跟冰鳍抢年糕失败的我一个人在院子里哭得伤心。
这是大的一位吧?叫火翼是不是?哭的怪可怜的!我听见有人温柔的低语着。泪水使眼中的世界微微有些曲扭我看见墙角盛开着的红色单瓣山茶花树下,站立着一位中年妇人。
她是客人吗?不然绝对进不了大门,也不会知道我名字的。可她是何时进来的呢?是谁的客人呢?哪一类客人呢?如果是现在的我一定能分辨清楚吧。可是当时我并没有多想,因为这位妇人看起来是那么文雅亲切,她白色长衣的衣角织着一枝优美的绯紫色花朵。
去我家吃酒吗?什么也好,让你吃到饱哦!她并不走近,只是轻柔的询问着,去吗?如果你去的话,我家的小姑娘也会很高兴的。
祖父曾告诉我,对于有些陌生者要装作视而不见。万一他们能发出声音,就一定要回答:不要问我,你去问我家大人。我也就这样说了。
这样啊白色长衣的妇人笑了起来,讷言先生你看,就等您一句话啦!
讷言是祖父的名字。
原来祖父在家啊我抬起头,看见祖父站在我背后檐廊的阴影下,戴着那付古旧的老花镜。冬日午后慵懒的阳光像金色的纱幕一样挂在他面前。不知怎么的,我忽然觉得好像等了祖父很久似的,忍不住又大声哭了起来。
这样哭个不停的小家伙你也不介意吗?那就没办法了,就带火翼去你家吧。祖父客气的接受了妇人的邀请,我们准备一下,晚上开席之前一定到!
真是件大喜事啊,我得快点回去告诉大家!讷言先生,夜路会有些难走,我家在旧城七巷,门前有棵很大的槿树的就是,请别走错了啊!那位气质高雅的妇人行了个礼,转身慢慢的走出了庭院。
织着绯紫花朵的白色长衣消失在视野里的时候,我听见祖父无可奈何的声音:看来还是不行,你依然不太会和他们相处啊他摸了摸我的头,叫我怎么能放心呢,火翼
记得刚刚还是中午,可是天很快就黑了,冬天的白昼真的很短。按照祖父的吩咐,我穿上了那身六岁生日时准备的石榴红对襟棉袄。在东北角的院门口等他。
不一会儿祖父就和妈妈一起来了,因为是去参加宴会的关系,妈妈穿上了那件孔雀翎花纹的新旗袍,那个时候穿旗袍的人非常少,这可是很时髦的。
人家说就请我和爷爷两位啊,妈妈可以去吗?我问祖父。
没问题没问题,多个人就多份热闹嘛!祖父大笑着,妈妈在一边微笑,并没与答话。
那冰鳍呢?我说着,忽然想起他抢走我那份汤年糕的事,还是不要带他了,那个坏家伙!
是啊这桌酒宴还是火翼去比较好透过老花镜的镜片,祖父笑得有些意味深长。
夜路真是很难走,旧城错综复杂如蛛网一般的小巷走多了就会有在原地打转的错觉,虽然平时对于我来说它们就像自家的庭院那么熟悉,可是今天,就好像不同的光线使人的容颜产生微妙的变化一样,小巷,变成了某种陌生的东西。
应该不算太晚的,可是路上只有祖父、妈妈和我三个人,初升的月亮把淡青的光芒洒在印着车辙的石板路上,太窄的道路使太高的白墙显得有些变形,像被无形的手朝着夜空的方向拉伸似的。被祖父领着不断朝前走,我的脚有些麻木,此刻视野里的砖墙和雕花门扉看起来就像不断被抽掉的蓝灰色屏风。
到底走了多久了呢?我家住观花巷,离旧城七巷并不是很远啊
爷爷,我们迷路了吗?我拉住祖父的衣袖。祖父从上方看着我,笑而不答。
会赶不上酒宴吗?我有些不安的询问着。
无可奈何的苦笑浮现在脸上,祖父的眼神则藏在老花镜片后面:我还以为这样就可以躲过呢,如果火翼想去的话,那就只好去了
原来您在这里啊!温柔的声音从黑暗的彼方响起,我们等了好久呢,迷路了吗
织着绯紫色花枝的白色长衣像一个水泡,从浓稠的黑暗里慢慢浮现出来,是白天那位优雅的妇人。
可不是,完全摸不着路!祖父不好意思的大笑着,你的家可真难找啊!
妇人掩口笑了起来:哪儿的话!不就在眼前吗?我带你们去。她伸手来拉我的手,我有些害怕,抬头看了祖父一眼,祖父并没有让我拒绝的意思,我也只好把手伸了出去。
那位妇人搀着我,还好她的手并不给人不舒服的感觉。只是随着她跨过了两滩积水,转过了一个拐角,一株巨大的槿树就呈现在我们面前。对于一向生得很纤细的槿花而言,这棵树实在太大了,两人合抱的枝干上点缀着苍绿的苔痕,而优雅的伸向夜空的枝头上则盛开着绯紫色的繁花,那位妇人衣角织着的花朵与它们一模一样。绉纱般的花瓣不时飘落下来后来我知道了槿花有另一个名字:一瞬之花。
这么明显的标志,为什么我们刚刚就没有看见呢
红色的灯笼从槿树下的黑暗中浮现出来,幼小的我不认识灯笼上写的字,只是将注意力全部放在了灯笼下虚掩的黑漆大门上。温暖的金色灯光从门缝里透了出来,伴随着微弱的笑语。
快点进来吧,大家都等急啦!那位妇人走在前面,一下子推开了门。
沉沦般的欢乐气氛瞬间奔涌了出来,就像盛夏正午的热风。那种众人发自内心的的欢喜呈现一种灿烂的金黄色调,模糊了我的眼睛。我和外公被众人簇拥着,走进了黑漆大门内的庭院。
庭院里挤了好多人,多到人的面孔看起来都不太清晰的地步。
讷言先生,等了你们好久啦,差一点就错过吉时了!人群中有人高喊。
三年前讷言先生帮我们赶走了百足一家,真不知道怎么谢你啊!又一个声音传来。
我都说不要谢了。外公有些为难得笑着,我也不是特意为了府上才对百足一家
那儿的话嘛,每年讷言先生都这么推辞,今年说什么也要报答你!白色长衣的妇人客气的打断了祖父的话,微笑着将视线转向我,再说,孩子们都六岁了,也长大啦
没错没错!那个就是火翼少爷吧,你看那双眼睛!一看就知道是讷言先生家的!
真是威风凛凛呢!
果然和小姑娘很般配!
又一轮热烈的议论开始了,这次话题的中心是我。不过他们的话让我非常不解,从来没有人用少爷这么古老的称呼叫我,也从来没有人夸赞我威风凛凛因为我是个女孩子啊!
讷言先生,你把谁带来啦!欢声笑语里,那位衣角描绘着绯紫色花朵的妇人忽然发出了锐利的惊叫,与她平日优雅的举止有些不太相称。
骚动瞬间在挤满了人的庭院内扩散开来,发酵成混乱的前奏。
精神全放在先生和小少爷身上啦,完全没注意到她!妇人指着妈妈质问着,这是谁!离她最近得我突然之间感到无法言喻的寒冷。
她不就是火翼的妈妈吗!祖父陪着笑脸,孩子大喜的日子,妈妈不来不太好吧
这样啊妇人的语气缓和了,放心的议论声也在庭院里扩散开来。似乎这里的人们都认为妈妈出现在这里是情理之中的事,可是却又不自觉的避开她身边的位置。
这可有些麻烦啦,讷言先生。这次轮到妇人陪笑脸了,令媳的衣服,实在太扎眼了
妈妈的那件孔雀翎花纹的新旗袍很好看啊,我不觉得有什么扎眼的。祖父客随主人便:那就让她在大门口等着吧。
真是不公平,这么冷的天居然让妈妈一个人在门口等!我立刻讨厌起这户人家来。
时候不早了,让我家小姑娘和火翼少爷见见面吧!妇人提醒着,人们立刻欢笑着让出了一条小路,我看见一位少女从小路的尽头,灯光昏暗的堂屋内走了出来。
这家的小姑娘真的和我一样是六岁吗?看起来完全象个大人啊!她穿着织了繁复的绯紫色花朵的白色锦缎旗袍,也许是很美的吧,可是年幼的我完全没有注意到。因为那时我发现不只是她,不只是那位优雅的妇人,这个庭院里不论男女,所有的人都穿着各色的锦缎衣服,每件衣服的图案千姿百态,但素材无一例外的都是这种绯紫色花朵槿花。这里的人是如此的偏爱槿花!
小姑娘很喜欢火翼少爷呢!穿槿花衣服的人们起着哄。那位说起来和我很般配的美少女似乎很满意我的眼睛,把它们当成了整装的镜子,在她靠近的时候,我看见她眉间一片如槿花花瓣一般精致而艳丽的绯红胎记。
她是你的新娘子!那位妇人指着槿花胎记得少女对我说。
新娘子?是可以吃的东西吗?走了半天,还被一群人围着说了许多莫名其妙的话,我实在是又饿又累,此刻食物是我最关心的问题。
这可怎么说啊反正娶新娘子的时候是要吃一顿的祖父被我问得有些为难似的,躲在镜片后皱着眉头笑着,好像在想什么。
而那位妇人似乎有些遗憾似的:看着火翼少爷和我们小姑娘站在一起就想到冰鳍姑娘,我家没有年龄相仿的男孩子,真是可惜啊
我立刻想起了年糕被抢走的事:才不要理冰鳍呢!总是跟我抢东西!
是吗!祖父忽然笑的有些古怪,你的新娘子可别让他给抢走了啊!
那可不行!我一定会把新娘子藏得好好的!我的话让庭院里的人们快活的哄笑着,开起了善意的玩笑。祖父则透过镜片注视着我,用一种奇妙的表情:藏在那里最后还不是都被冰鳍找到!
一点也不错,虽然和我一样都是寻找失物的高手,可是冰鳍的准确率更高,因为除了拥有和我一样的眼睛之外,冰鳍还有一双可以倾听来自黑暗中无形之物声音的耳朵啊!
你准备怎么办呢?平时你都是怎么对付冰鳍的?祖父的话里有一种劝诱
我当然有办法!吃到肚子里最保险啦!我得意洋洋的大声说。
不安的低语瞬间滑过整个庭院,又渐渐被沉默所吞噬。我没有发现身边的人们挪动着,让到了远处。槿花衣纹的妇人呆呆的看着我,战战兢兢:到底是讷言先生家的不是开玩笑吧?你真的要吃吗?
不是你说的吗?因为疲劳和饥饿,以及小孩子的任性。我的脾气也坏了起来,你说来你家什么也可以吃,让我到饱的!
如同弓弦紧绷一般的短暂沉默之后,忽然谁的大喊爆发出来:不得了!他说什么都要吃啊!
快逃啊张惶呼喊的语尾像被吞吃了一样蓦然的消失在夜色里。我听见奇怪的声音,像无数昆虫翅翼在扑闪一样的声音。
如同离弦之箭般,不可收拾的光流缭乱的掠过我的眼前,像除夕夜的烟火。
祖父拉着我的手,镇定的向门口移动。似乎有许多不成形的东西在晃动逃逸,像轻柔但却纷乱的羽毛一样不断扑打到我脸上。我不得不闭上眼睛。
对不起啊,讷言先生,可能不能把小姑娘嫁到你家去啦!我听见那位妇人乞求的声音。
真失礼,我家可是很期待呢!一向宽容的祖父忽然不依不饶起来,我们可再也不来啦!
忽然之间,混乱的声音和羽翼的触感消失了我知道我们已经跨出了大门。
我睁开眼睛,眼前是漆黑的夜路。我学着大人那样叹了口气:结果还是什么也没吃到
祖父微笑了起来,托了托眼镜:想不到火翼也很厉害嘛!
什么啊?我不解的抬头看祖父。
这家人也没有什么恶意,可就是纠缠不休的。祖父叹了口气,我让你和冰鳍不要透露真实的身份也是为了防这样的人家,万一让冰鳍和这种人定了亲可就一点办法也没有啦!
这是怎么回是啊,爷爷?
我本来是想让火翼你和她家的姑娘定亲的。你和女孩子的婚约当然是无效的,日后就用这个来搪塞这家人,祖父松了口气似的大笑起来,这招可有点险呢,万一那个女人发起狂来
会吃掉我吗?我有点害怕,大喊起来,爷爷就是比较偏心冰鳍嘛!
火翼这样看爷爷啊?爷爷好伤心祖父装出要哭的样子,随即又笑着摸了摸我的头,你们两个都是我的宝贝嘛!而且火翼把他们吓跑啦!相当能干呢!他们可以为你要把他们都吃掉呢!
啊?我吃他们
看来我是多虑了你也许比我想的更善于和它们相处呢。祖父抬头看向幽深的黑夜,而且我也不可能永远保护你们
那可不行,爷爷不在的话,那家人再找来怎么办?
祖父笑得眼镜都要掉下来了:不会了不会了,就是防这个,我在门口留下她们害怕的东西啦!
当时我没有去思索祖父的话,因为我忽然发现妈妈并没有跟上来。我急得几乎要哭出来了。祖父推着滑到鼻梁上眼镜:别担心,一回去准能见到妈妈!她和我们走的不是一条路啊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祖父这句话说得意味深长。
东北角的家门口,我看见冰鳍坐在台阶上,好像等了很久的样子。一看见我他就站了起来,拍了拍牡丹纹紫棉袍上的灰尘:爷爷!他叫我身后的祖父,声音有些委屈:爷爷果然比较喜欢火翼呢,都只带她出去
祖父一手摸着我的头,一手摸着冰鳍的头:这回你可要好好谢谢火翼啊,冰鳍
冰鳍拉着我的衣角,我知道这是他道歉的表示:火翼一定很害怕吧,下次换我保护你。
我们并没有抬头去看,但都知道得很清楚祖父笑了,笑得很安心。
妈妈呼唤我们的声音忽然从大门内传来,我们回头望时,妈妈已经换了家常的衣服,正穿过天井向我们走来。她果然先到家了!
转过屋檐的阴影,西斜的阳光正穿过院墙上的花窗,照在妈妈脸上
怎么会有阳光呢?现在不是深夜吗,刚刚举行了槿花宴的黑夜啊我回过头想向祖父询问。冬风卷着枯叶,掠过门前的青石板街面,疾驶向未知得远处那里,没有任何人的影子
掌心中似乎有什么,硬硬的。我低下头,发现祖父的老花镜正静静的躺在我手里
多年之后我向家人问起槿花之家的事,可所有人都说我们并没有住在旧城七巷的熟人。虽然那里是有棵槿树,但树下绝对不会有挂红灯笼黑漆大门的,因为那一带都是高大的院墙。
连妈妈也不记得那一场夜宴了。我提醒她那夜她穿着孔雀翎毛花纹的新旗袍,可妈妈立刻生气了,说那件旗袍冬天做好,夏天准备拿出来穿时却怎么找也找不到了。
婶婶和祖母也笑我说那段回忆漏洞百出冬天哪来的槿花呢?
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穿着六岁生日的小棉袄跟祖父去参加宴会,可是祖父在我四岁那年就已经过世了!
准是做了个梦,妈妈下了结论,小孩子分不清现实和梦境的差别。
听到大人这么自信的话,我和冰鳍看了对方一眼,偷笑了起来我们知道的,旧城七巷的槿树那里是住了不少的人家,他们就靠这槿树为生。这株巨树是它们的居所、食物、甚至陵寝。
妈妈的那件孔雀翎毛旗袍是找不回来了。因为正是它以妈妈的形象跟着我们去赴那场槿花夜宴,它还在那家人的门口等着,一直等到今天。
不信可以看槿树根部的苔痕,苍绿的苔钱结成了一个又一个孔雀翎眼的形状。就像在树上围了一匹华丽的锦缎。
因为有它在的关系,那个温柔文雅得妇人和她眉间有槿花胎记的女儿再也没来找过我们。她们是不敢出门的了,不奇怪,孔雀本来就是她们最怕的东西嘛。
偶尔我和冰鳍路过这棵槿树的时候,会看见两条美丽的白蛇攀在高高的枝头乘凉,其中那条额上有绯紫色槿花斑纹的那条每次看见我都躲进树洞里去,然后探出头来偷偷看我,好像很害羞,又好像有点怕我的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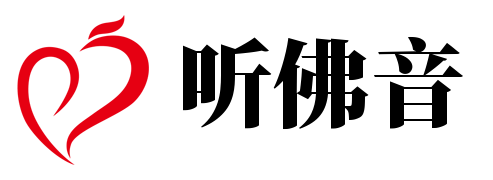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