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真法师:佛陀的日常生活
近读汉译《四阿含经》发现了不少关于佛陀日常生活的事实,不但趣味隽永,实际上对我们作弟子的也具有极大的启发性和示范性;因此辑录出来,作为南传佛教国家纪念佛陀涅槃二千五百周年的随喜功德,使我们共同在佛陀的慈光照耀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继承遗志,发扬佛教的事业而努力。
遇有原文晦涩和过于杂冗的,还有像一个中心内容相同的故事,却用大同小异的词句,写成两篇或两篇以上而散在几部经里的;为了便利读者,这些地方,我都企图在不失原意下,尽可能地把它变成现代的语文。
一
在日常物质生活方面,佛陀是极端主张朴质、节省的。如约衣说,佛陀就是主张著粪扫衣的。(《大乘义章》卷十五说粪扫衣者,所谓火烧、牛嚼、鼠啮以、死人衣等,弃之巷野,事同粪扫,名粪扫衣,行者取之,浣洗缝治,用以供身。这是说一般居民将事同粪屑扫出去了而倾弃在巷野的破烂布条,比丘拣取出来,加以浣洗,缝治为衣,就叫粪扫衣。)在《增一阿含》卷九、《杂阿含》卷三十八内,有着这么一个相同的故事:佛在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尔时尊老难陀,著极妙之衣,色耀人目,著金厕履屣,复文饰两目,手持钵器,欲入舍卫城乞食,恰好给几个比丘撞见了,就直认为是离经叛教的事情,纷纷去向佛陀投诉;佛陀派人把尊者难陀唤回,进行说服教育,不但要他经常著粪扫衣,还要他经常应赞叹著粪扫衣者。再约食说,佛陀是主张日中一食的。《增一阿含》四十六、《中阿含》五十一内,也有着这么一个相同的故事:佛在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告诸比丘:我恒一坐而食,身体轻健,气力强盛,汝等比丘,亦当一食。尔时跋提婆罗白世尊言:我不堪任日一食。所以者何?气力弱劣。结果跋提婆罗因不堪任日中一食,就隐匿了三个月不敢和佛陀见面。《中阿含》卷五十一,说佛游迦尸国时,也拿自己做范例,告诸比丘,应日中一食;结果有二比丘,一名阿湿具,一名弗那婆修的,都怀着抵触情绪,不能接受佛陀的意见。《杂阿含》卷四十二内,还说波斯匿王,其体肥大;就是向佛陀作一下礼,也感到气息长喘,惭耻厌苦;佛陀特为他唱出了一首偈颂,要他每食知节量不要贪图口腹,太吃多了。波斯匿王很欢喜地接受了佛陀的意见,并要一个名叫御多罗的少年,在他每次进食时,唱诵佛陀为他歌唱出来的偈颂,实行食物定量制,居然也渐至后时,身体臃细不再肥大得气喘发愁了。最后应该讲到住了,佛陀是主张树下宿露地坐冢间坐的。根据《四阿含》里的材料,佛陀个人虽说在这些地方住宿的时间不多,但亦约有百处以上是说佛陀住在所谓叶屋里的。又《中阿含》卷六,给孤独园长者说他自己当初想在舍卫国购买地皮,来建筑屋宇供养佛陀时,舍利佛为佛陀提出的条件,也只是希望画不喧闹,夜则寂静,无有蚊虫,亦无蝇蚤,不寒不热,并没有希望做到怎样堂皇富丽。《增一阿含》卷二十说佛在阿罗毗祠侧,尔时极为盛寒,树木凋落,手阿罗婆长者子白世尊言:不审宿宵之中,得善眠乎?世尊告曰:如是童子,快善眠也。时长者子白佛:今盛寒日,万物凋落,然复世尊坐用草蓐,极为单薄;云何世尊作如是说:我快得善眠?从这些记叙里,我们还是可能肯定佛陀的住处,是朴质刻苦的。《增一阿含》卷四十五,佛陀告诫比丘,如要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脱成就,解脱见慧成就,就应当先成就十一法。上面所说的粪扫衣、日中一食、树下宿等,皆是包括在这十一法以内的。同《经》卷五,更说其有叹誉著五衲衣者,则为叹说我已,其有毁辱著五衲衣者,则为毁辱我已;其有叹说在冢间坐者,则为叹说我已,其有毁辱在冢间坐者,则为毁辱我已,其有毁辱一食者,则为毁辱我己。试想佛陀直把叹誉这种刻苦生活的,引为叹誉自己;毁辱这种刻苦生活的,引为毁辱自己。在佛陀思想上对这种生活是何等的重视了。佛陀弟子中,如尊者迦叶、尊者阿那律陀等,在日常物质生活方面,都是能坚决贯彻这种精神的;因此也特别获得了佛陀的欢喜赞叹。甚至有一次,佛特别分半座给与迦叶,示以特殊的光荣。(见《杂阿含》卷四十一)所以佛陀住世时,一般地说,出家两众弟子,在日常物质生活上,大都能耐得住淡薄的。
现在根据汉译《四阿含》里的材料,我还想抓出几个问题来谈一下。一、佛陀为什么要强调这种淡薄刻苦的生活?一般地说,当然是为了专精道业,不能把心志沉溺在物质的享受上,使之浪费时间、金钱和精力。但是,除了这,我认为还有两个比较主要的原因:甲、当时社会的经济生活太艰苦了。如《长阿含》卷二说,佛在跋只国游化时,因为彼土谷贵饥馑,乞求难得。不能不将常随的比丘众遣散到其他的国度里去。《增一阿含》卷四十三说,有一次,因为舍卫城谷米涌贵,乞求叵得,随侍佛陀的一些弟子,竟自动地集合普会讲堂,讨论对策,有主张到摩竭陀国去,有主张到拘留沙国去,也有主张到拘深婆罗捺城去的。意见纷歧,乱哄哄地搅做一团。《杂阿含》卷三十二说,佛在摩竭提国游化时,有一个名叫刀师氏的聚落主,竟责难佛陀说:今云何于饥馑世,游行人间,将诸大众千二百五十,从城至城,从村至村,损费世间,如大雨雹!?雨已,乃是减损,非增益也!《杂阿含》卷四十一,更说尊者阿难,住王舍城耆阇崛山中,世尊涅槃未久,时世饥馑,乞食难得,不能不率众转移到南天竺去,当时就有三十个青少年比丘,因此而舍戒还俗了。乙、佛陀在思想上深刻地体会到劳动人民创作的辛勤和生活的艰苦,如在《增一阿含》卷六内唤醒弟子们说受人供养,甚为不易;情感所激,就不容不主张淡薄刻苦的生活了。因此我想佛法传入中国时,由于中国当时的社会情况,毕竟与佛陀住世时的印度不同,故佛法传入中国后,一般出家比丘,都不能实践印度的乞食制。到了唐朝,一些昂头天外,牢笼不住的禅宗大师,更别开生面,多数欢喜在水边林下,犁云锄月,使佛法与自己活生生的劳动打成一片,向石头土块里演唱宗乘,接引来学。这就不能不说没有它的客观原因了。二、佛陀虽强调淡薄刻苦的生活,但在《四阿含》里却又有很多的地方,极力排斥当时的所谓苦行外道,这又是什么原因?应知苦行外道,是以苦行自负的,直认苦行为道,或认苦行为证道的唯一途径的。佛陀主张淡薄刻苦的生活,主要是在减轻当时社会人民的负担,并借这来消磨自己贪瞋痴慢的习气,在自己本分上是应该这样做的,丝毫没有使个人可能自负的地方。如在《中阿含》卷二十一内,佛陀就恳切地向弟子们说:或有一人著粪扫衣,余者不然,故自贵贱他,这就不能算一个真正学习佛法的人了;或有一个常行乞食,或复一食,过中不饮浆,余者不然,故自贵贱他,这就不能算一个真正学习佛法的人了;或有一人,或止露地,或处冢间,余者不然,故自贵贱他,这就不能算一个真正学习佛法的人了。淡薄刻苦的生活,固然是佛陀所倡导的;但假使弟子们认为自己能实践这种生活,就自负不凡,认为自己能行人之所不能行,忍人之所不能忍,因而在思想上造成自贵贱他的趋势,这就与佛陀原意大相违反,不能不痛加申斥,说这样做,就不能算作一个真正学习佛法的人了。至于佛陀通常所说的道,主要即指缘生无我的真理。理解缘生,即应掌握人类社会相依共存的规律,理解无我,即应克服自私自利的恶念而使个人利益服从于社会整体的利益;所以佛陀所说的道不是虚玄的,而是具有其现实意义的。《中阿含》卷五十七内,说有一异学名叫箭毛的,他认为佛陀能傅得弟子的尊敬承事,常随不离,是得力于粗衣知足、粗食知足、少食、粗住止床坐知足和宴坐这五件事。当时佛陀就反对他这种看法,说自己能取得弟子信仰尊重、常随不离的,主要是由于自己能坚持真理,启发弟子们的智慧,帮助弟子们提高品德,使之能在生活上加强信心和力量。从这些地方,我们可以充分理解佛陀是主张淡薄刻苦生活的,但决不是单纯强调这种形式,尤其是与当时的所谓苦行外道是有着极其严格界限的。三、我们还要问的,在当时佛陀个人能否贯彻自己的这种主张呢?根据许多材料,可以毫不隐讳的答复,佛陀是不能贯彻的。如《中阿含》卷十三说世尊回顾告曰:阿难,汝取金镂织成衣来,我今欲与弥勒比丘。《杂阿含》卷四十一说世尊告摩诃迦叶言:汝今已老,年耆根熟,粪扫衣重,我衣轻好。力劝尊者迦弃改著自己的轻好衣,不要再著粪扫衣了。至于饮食。在四《阿含》里记叙的,当佛陀来接受在家信众供养时,绝大多数都是异常丰美,几乎触处可见。又如当时佛陀所住的祗树给孤独园、竹林加兰哆园、奄婆娑梨园等地方,不但风景优秀,就是房屋也是十分漂亮的。这些不都是佛陀不能贯彻自己主张的好证明么?佛陀为什么不能自己贯彻?为什么要使自己陷于矛盾?这也是值得我们研究而且应该研究的。最明显的原因,我认为:甲、当时佛陀及其弟子的日常物质生活,全都是仰给在家佛教信众供养的;信众既然根据个人经济情况或者感情上的信仰程度不同,把衣食住等都预先准备好了,假如没有特殊原因,佛陀也只好不加简择,遇啥吃啥,遇啥穿啥,不容再麻烦人家了。乙、佛陀虽强调淡薄刻苦的生活,但在自己的思想认识上,觉得还有比这更更高贵的东西;为了使信众能接近、享有这更更高贵的东西,在淡薄刻苦的生活方面,非要打些折扣不可,当然也就会毫不吝惜地打它一些折扣了。譬如说,比丘积蓄多余的衣服,在佛陀原来是不许可的;但《中阿含》卷二十七内,佛陀向得了最上慧观法的比丘说:我说不得蓄一切衣,亦说得蓄一切衣。为什么?若蓄衣便增长善法,衰退善法者,如是衣我说不得蓄;若蓄衣便增长善法,衰退恶不善者,如是衣我说得蓄。如衣、饮食、麻榻、村邑,亦复如是。善法是适当的注脚,就是利益安乐众生的事业。衣,应不应蓄?应该从增长利益安乐众生的事业上去考虑问题,不能死执成法,把自己变成一个教条主义者。不过这样做,在没有获得最上慧观法的比丘,是不十分容易搞得通的。又《增一阿含》卷二十四内,说有一个原本信仰佛陀的优婆迦尼长者,他的哥哥和姊姊,也在同一时间内接受了佛陀的法化。当时的阿阇世王,非常欢喜,给他送去了许多上上品的饮料和食物,他接到了,便作是念:我竟不闻世尊说,夫优婆塞之法,为应食何等食?应饮何等浆?并随即派人到佛陀那里去请示开示,佛陀也是叫他应当从增长利益安乐众生的事业上去考虑问题。从这些地方,我们可以充分理解,佛陀在强调淡薄刻苦的生活上,固然有它的严肃性,同时也是具有灵活性的。佛陀不能贯彻自己的主张,这不但不能委为佛陀的过失,相反地显示了佛陀的智慧深湛和人格伟大,因为他一切活动,都是从利益安乐众生的事业出发,决不是泥执不化的教条主义者。
二
佛陀在物质享受上,虽强调淡薄节省;但对于日常穿衣吃饭的这些琐事,却又十分认真,一点都不肯马虎。《中阿含》卷四十一说:弥莎罗地方有个权威人物,名叫梵摩,他虽衷心倾慕佛陀,企图相见,却又怕佛陀名不符实;因之踌躇不决,特地请求学者优多罗,前往实地观察。优多罗随着佛陀住了四个多月,在他回到弥莎罗晤见梵摩的时候,居然提出我欲诣彼沙门瞿昙从学梵行,掳优多罗口头所描绘的,例如著衣,佛陀在质料上,固然十分朴素,但却十分整洁。衣服穿在身上,不长不短,恰好合身,既不紧紧地箍在身上,也不是空荡荡地显得宽大无边,即使刮起大风,也不会把披在身上的衣服卷飞而去。佛陀披着衣服在街上走时,两目平视,步履轻捷,不会有尘土飞坌起来。佛陀在《增一阿含》卷二十四内,说沙门出家,有五毁辱之法。 一、发长,二、指甲长,三、也就是衣裳垢坌。足证佛陀对衣著十分整洁,是能将朴素、适用、美观统一起来而 具有一定艺术性的。至于佛陀食与住的情况,在优多罗口头和许多经文里也有很好的描述,我想读者定能举一反三,用不着再事摘录了。又:宴坐、经行,亦机为佛陀日常生活的惯例,在《四阿含》里,真个随手翻检可得。当佛陀经行时,往往悄然从背后跟上一个或者好几个弟子,在佛陀发觉或有兴会时,往往互相酬问,不自觉地形成一种小型法会;亦有跟上了半天,佛陀还茫然无所知的。《杂阿含》卷四十九,说佛陀住摩鸠罗山,于夜暗时,天小微雨,电光郯现,佛陀还坚持出于房外露地经行。最有趣也最耐人思省的,《杂阿含》卷四十二内,说佛在东园鹿子母讲堂,东荫荫中,露地经行,当时有个异学名叫婆罗豆遮婆的,竟气势汹汹地骂上门来了;他看见佛陀还是安步经行,宛若无事,就又追在背后骂不绝口;等到世尊经行已竟,住于一处时,他还以胜利者的姿态,逼问佛陀:瞿昙伏耶?佛陀却开示他说:你无故侵犯人,想压倒人了,来造成自己的胜利,结果只能替自己树敌结怨,别无好处;因为伏者的内心,即使天睡梦中都不会忘记自己的仇恨,他会刻骨地企图报复的。我们还是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不强分什么谁胜谁伏吧!
三
澡浴,也是佛陀一种特殊的嗜好。《中阿含》卷二十七说世尊则于哺时,从宴坐起,堂上下来,告曰:阿难!共汝往至阿夷罗和帝河浴。同《经》卷二十九说世尊将尊者乌陀夷往至东河,脱衣岸上,便入水浴。浴已还出,拭体著衣。《长阿含》卷三说佛陀在涅槃前,还和许多弟子到拘孙河洗了一次澡。《增一阿含》卷六,《杂阿含》卷四十四,还有着这么一个内容相同的故事:住在孙陀罗江边的一个异学,跑到祗树给孤独园,邀请佛陀到孙陀罗江去洗澡,佛陀问他为什么必须要到那条江里去?异学白世尊曰:孙陀罗江水,是福之深渊,世之光明,其有人物在彼河水浴者,一切诸恶,悉皆除尽。佛陀当时就批评这是迷信,说他这样做,是犹盲投于冥!假如不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涤荡残存在思想感情上的污垢,那就是宿罪内充躯,彼河焉能沐!佛陀并说,如其阇行不清净,不但恒河、婆修多河、孙陀利江里的水,不能洗涤,就是在形式上举行布莎也是空的。
《增一阿含》卷二十八内,佛陀还向弟子们提倡建筑浴室。说有了浴室,对人民有很多好处:一、除风湿,二、治疗一切与之相适应的疾病,三、除污垢,四、使身体轻便,五、使身体肥白。不但提倡建筑浴室,在同卷经文内,还提倡施人杨枝。(《毗尼日用切要》:杨枝,律中名曰齿木。又《南海寄归传》卷一说每日朝旦,须嚼齿木揩齿,,盥漱清净,方行敬礼。因为在佛陀时代,根本谈不上今天使用的牙刷牙膏,只好教人折取细嫩杨枝,截为断段,将一端用齿啮羢了,即用以揩齿,名曰齿木)佛陀说用杨枝揩齿,不但可使口腔不臭;并能帮助消化和减轻眼内的火热;因之赞叹施人杨枝,也是有功德的。
四
佛陀不但对个人生活,重视清洁卫生,对环境的清洁卫生,也是十分重视的。《中阿含》卷八说:佛陀在毘舍离时,有一天,望见天色晴明,将许多东西抱出,抖了,抹了,放在太阳里晒;不料后来天气渐变,黑云蔽日,眼看要下雨了,佛陀又赶忙将东西抖了,抹了,抱到房内去;可是收拾好了,雨还没有落下来,佛陀又赶忙拖着一柄扫帚,将自己弄脏了的地面,扫得干干净净。《增一阿含》卷二十五说:佛陀告诉弟子,在扫地时,应先辨别风向,好好将灰屑扫聚一处,畚了出去;还要仔细检视,看地面扫干净了没有?不然,到处坌的都是灰,甚至粗心大意,地面还留积一些讨厌的灰屑,这是不能成就扫地功德的。若扫塔内,先应洒水;遇有瓦砾,要捡出去,凸凹不平的地方,也要动手修治,使之平整。从这些地方,我们不难体会佛陀是具有劳动热情的,对公共卫生工作,更是非常活跃与爱护的。
五
佛陀不但重视公共卫生,也十分重视公众的利益。《增一阿含》卷二十七内,佛陀勖勉比丘,当念修行此五惠施。一者造作园观,佛利公众游憩观赏;二者造作树林,绿化名胜风景区和城市、乡村、道路,增加公众生活里的美感;三者造桥梁,四者造作大船,五者在路旁造作房舍住处(《杂阿含》卷四十二,为回路造房舍,行路得止息。)尽量发展交通事业,使公众在行程中,感到舒适便利。佛陀就是勖勉我们出家比丘,把努力这种公众事业,作为自己修行的。《杂阿含》卷四十二说,波斯匿王请求佛陀开示布施功德,最后佛陀也是拿这种公众事业相勖勉;并且认为他是国王,力量很大,只要在实际上能努力去做,那就将譬如重云起,雷电声震耀,普雨于土壤;百卉悉扶疏,禽兽皆欢喜,田夫并欢乐!我们不难窥测佛陀内心,是如何地强烈希望当时人民能够获得幸福愉快的生活呀。
六
《增一阿含》卷五:一时佛在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告诉比丘:其有瞻侍病者,则为瞻侍我已;有看病者,则为看我已。所以然者,我今躬欲看视疾病。并且把侍护病者,看望病者,认为是施中最上,无过是施。因此在出家弟子中,像尊者婆耆舍、叵求那、跋迦叶、均头,甚至是一个年少的新学比丘病了,佛陀都亲自去前往探视慰问,并且发动一些比丘前往慰问,又随时向其他的比丘探询病者的情况。像这类的描画,在《四阿含经》内是相当多的。不但对出家比丘,就是许多在家信众病了,佛陀也非常关切他们,常常亲身前往探视慰问。这一类的资料,在《杂阿含》卷三十七内特别突出。又《增一阿含》卷二十四内,佛陀告诉病者,应该注意下面五项事体:一、慎重选择饮食的质料;二、不要随时滥喝滥吃;三、要信任医药;(遍读全经,却都没有发现像中国习俗,偏不信任医药,而去搞什么敕茶画水或者求香灰求药签的);四、设法排遣自己的忧愁和瞋恚,常使精神上保持宁静和愉快;五、对待护自己的人,要体贴,不要闹脾气。同时佛陀告诉侍护病者的人,也要注意五项事体:一、要具有医药常识;二、善于言谈,常向病人温慰宽解;三、不要贪睡,对于病人,最好能做到先起后卧;四、要细心耐烦,不能贪图病人的饮食;五、能方便为病人说法。佛陀逝世已经有二千多年了,不但这种深切同情病人的心思,值得我们作弟子的学习;就是所提出来的养病侍护病人的方法,也还是具有极大的现实意味,是我们应该重视的。
《增一阿含经》卷十八内,说王波斯匿,与世尊办种种饮食,观世尊食竟。白世尊曰:世尊亦当有老病死乎?世尊告曰:如是,大王,如来亦当有老病死为什么?因为我今亦是人数,佛陀晚年,常感背脊痛,经内有很多地方,都提到了这一回事。《增一阿含经》卷二十七、《杂阿含经》卷四十四的,还载有这样一个大同小异的故事:佛在拘莎罗人间游行,至浮梨聚落,住天作婆罗门奄罗园中,尊者优婆摩为侍者。尔时世尊患背痛,告诉了优婆摩;优婆摩跑到天作婆罗门的住宅内,恰好碰见他的理发,优婆摩将这消息告诉了他,天作赶忙以满钵酥,一瓶油,一瓶石蜜,使人担持,并持暖水,随尊者优婆摩诣世尊所,以涂其体,暖水洗之,酥蜜作饮;世尊背疚即得安隐。就是佛陀将要在双林入灭的时候,还在向弟子们诉说自己的背痛。
七
佛陀平常对于自己弟子的态度,不但慈爱、坦率,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还表示了相当的尊重。《中阿含经》卷五十六说:有一次,世尊将尊者阿难,往至梵志罗摩家,尔时梵志罗摩家,众多比丘,集坐说法,佛陀马上招呼阿难,不要敲门,就和阿难悄然屏息,站在门外,深怕里面发觉了。待诸比丘,说法讫竟,默然而住;佛陀才有意识地咳了一声,用手敲门;等到众多比丘,发觉了佛陀的声音,知道自己最敬爱的导师也来了;我们不难想象,大家是以如何欢欣、激动的心情争相跑出来迎接佛陀的。《中阿含经》卷五十说:尊者乌陀夷在阿和那这个地方乞食时,无意中发现了佛陀也在这里乞食,他因很久没有会见自己的导师了,当时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欢喜。于是暗自忖度:假如佛陀今天到那个林野经行时,我也暗自跟在佛陀的背后经行;假如佛陀今天到那个林野宴坐时,我也要暗自在佛陀的附近,找个适当地方宴坐。虽然结果都满足了他的愿望,但是宴坐时,心情总还牵挂佛陀,怎样也按不下去;于是就只好向着佛陀跑去了;佛陀发现了乌陀夷,惊喜地喊着他的名字,问他是不是安隐快乐,气力如常;问他在生活上有什么困乏。《中阿含经》卷四十二说:有一天,眼看太阳要落山了,佛陀还在荒野内踽踽独行,于是就向一个不相识的窑匠要求,希望能到他的空窑内借宿一宵。窑匠说:对不起,里面已先有一个沙门借住了,只要他同意,我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佛陀跑到窑门边,看到里面果然端端正正地坐了一个比丘;遂又向比丘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比丘说:只要主人答应了,我还有什么意见哩。先生,你看这里面的草不是已垫好了吗,只要先生高兴,就请进来住吧。佛陀遂到附近把脚洗了,再回入窑内,将尼师坛铺在草上,自己也就安安静静地坐下来了。天麻麻亮了,佛陀瞥见比丘还是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神志恬适宁静,不觉油然起了一种尊敬的念头,遂向比丘问道:汝师为谁?依谁出家学道受法?比丘才说自己名字叫弗迦罗娑利,师父就是释迦牟尼佛。佛陀听了,真是又惊又喜,随问:你认得自己的师父么?比丘说:惭愧,我还没有见过自己师父的面哩。佛陀又自动为弗迦罗娑利说了一些修行的道理,使他在思想上彻底明确了觉白净法,断疑度惑,不复由他,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同时也使他逐渐明确了现在替自己说法的,也正是自己平日所衷心倾慕的师父,不觉激起了弗迦满腔悲喜愧悔的复杂心情,倒身向着佛陀礼拜说:师父,请您慈悲我吧!您看我如愚如痴,不识良田,遇到了自己最尊敬的师父,还泛泛地喊为先生一点礼貌都没有,这是多么可耻的罪过。佛陀安慰弗迦罗婆利说:不错,把自己的师父喊作先生,这不能不说是愚痴;但是,你这不是有心,原来你就不知道呗。同时你更应该明确,任何罪业,只要自己能够真诚忏悔,不复更作,罪业也就如霜遇日,潜消于无形了;搁在心里,反而会变成自己的障碍,这是不能不注意的。《中阿含经》卷十九说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尔时尊者阿那律陀,住娑罗逻岩山中,距离给孤独园不还,尊者阿那律陀,过夜平旦,著衣持钵,入舍卫乞食,见尊者阿难亦行乞食。见已,语曰:贤者阿难,当知我三衣粗素坏尽,贤者今可倩诸比丘为我作衣于是世尊见尊者阿难,手执户钥,遍诣房房;见己,问曰:阿难,汝以何事乎执户钥,遍诣房房?尊者阿难白曰:世尊,我今倩诸比丘,为尊者阿那律陀作衣。世尊告曰:阿难,汝何以故不倩如来?阿难随即乘势合掌向佛:唯愿世尊往诣婆罗逻岩山中,为尊者阿那律陀作衣。佛陀率领阿难及诸比丘到了山里后,大目犍连,亦在众中,于是世尊告曰:目犍连,我能为阿那律陀舒张衣裁,割截连缀而缝合之。目犍连赶忙说:世尊,先请您裁好以后,还是让我们大家来连缀缝合吧。世尊很高兴地将布舒张,量裁好了,分别交给大家连缀缝合;眼见快要缝合好了,才喊着阿那律陀说:你应该感谢大家,为大家说说迦絺那法;我现在觉得有些腰痛,要休息一下了。《增一阿含经》卷三十一说:尊者阿那律因双目失明,在摸着缝补衲衣时,自己不能穿针,于是就纵声喊道:有发心修福的么?请快快来帮我穿针。佛陀就抢上前去替他将针穿好了。阿那律说:世尊,您怎么来了呢?我是在喊世间发心修福的人呀,难道世尊的福报还没有满足么?佛陀笑向阿那律道:将获众生,在众生面前修福,我是尽未来际都不会感到满足的。应知将护众生,在众生面前毫不疲厌地修福。这是佛佛相授,祖祖相承的不二法门,也是佛法能够久住世间的真髓,舍却了这点灵丹妙药,眼见佛都就只有变质和灭亡,这是我们佛弟子应该加倍警惕的。
八
佛陀不但对自己的弟子,无论对任何人,除了坚持真理外,都是诚恳、亲切、慈蔼、谦谨的。个别的故事,暂置不谈。即如用共相问讯面相慰劳的词句,来描写非佛教徒与佛陀会见的情景,在四《阿含经》里,可能亦在百处以上。如相共相,这都决不是单方面的动作,足见佛陀平日在思想上不仅尊重自己,也是非常尊重别人的。现在只从《杂阿含经》卷四内,拈出几节经文,来做具体证明。一、有年少婆罗门,名优多罗,来诣佛所,与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已;二、有年少婆罗门,名优婆迦,来诣佛所,与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已;三、有长身婆罗门,乘白马车,诸年少婆罗门,前后导从,持金柄伞盖,执金澡瓶,出舍卫城,诣世尊所,面相问讯慰劳已;四、有年少婆罗门,名僧迦罗,来诣佛所,与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已;五、有生闻婆罗门,来诣佛所,与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已。面相问讯慰劳,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主客双方,面对面地互相问讯,互相慰劳。年少,足见资历不深,佛陀竟亦毫不轻慢,俨然如接大宾,面相问讯慰劳;乘白马车、持金柄伞盖,这又是何等显赫?佛陀既不拒诸千里之外,也不捧而置之九霄云上,还是平等平等,面相讯慰劳。这已经足够我们叹服了。至于婆罗门,在许多佛弟子心目中,是一向认为自己隔了一层的异教徒。最欢喜存着狭隘观念的;而佛陀当时却偏能水乳交融,殷勤接待,面相问讯慰劳。
九
佛陀日常说法,多喜以戒施并提,所谓戒论施论的词句,仅在《中阿含经》内,恐亦不下五十处。据我体会,戒的精神,主要是不侵损他人的权利和生命;施的精神,主要是还要进一步去帮助人家。如通常说施有三种:一、财施,就是要用自己的财物和体力脑力(即所谓内财。)。去帮助人家,使之得以减轻苦恼,增加快乐;二、法施,主要是启发别人的智慧,使之能发现真理,坚持真理;三、无畏施,是要他使人民脱离怖畏,不感受任何恶势力的威胁与侵袭。根据今天世界的情况来说,戒与施的精神,还是非常迫切需要的。
十
我并不否认佛陀广大深妙不可思议的境界,但我认为佛陀是人的升华,是由人的本位进修而成功的。假如在人的基础上,做得不太牢实,那是很危险的,是不可能上升而成为圣者的。因之我在辑录佛陀日常生活时,都是从人的角度出发的,可能易知易行的。那么广大深妙不可思议的境界,是平地上的楼阁。我们目前最需要的,还是牢实的地,因之那些广大深妙不可思议的境界,我都从略了。
十一
佛陀的法身,是常住不灭的;佛陀的智慧功德,存活在广大的人民心里。只要我们作弟子的,能够掌握佛陀日常生活的精神,用以作为自己光辉的榜样,亦步亦趋,不屈不退,佛教是会发出更强烈更绚烂的异彩而永耀于人寰的。
(原载《现代佛学》一九五六年第五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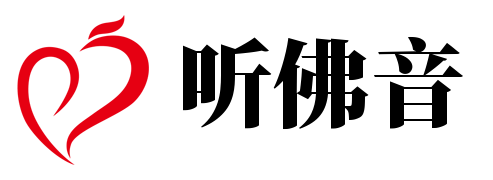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