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烂陀寺的佛像和犍陀罗造像的东传
那烂陀寺的佛像和犍陀罗造像的东传
那烂陀寺是中世纪佛教造像的盛地。遗址间可以见到形态各异的造像,或站立,或坐禅,或说法,无疑是一场视觉和精神的盛宴。除了断壁残垣上的石刻造像,大部分出土的造像陈列在那烂陀博物馆里,多为笈多王朝时期的秣菟罗和萨尔那特风格,以及波罗(或称帕拉)王朝时期的波罗样式。
秣菟罗造像是典型印度本土风格。秣菟罗位于恒河支流朱木纳河西岸,是通往中印度的门户,自古是繁荣的贸易要冲,也是婆罗门教、佛教和耆那教的中心地带。贵霜王朝时期,秣菟罗地区就开始了佛像的雕刻,而在笈多王朝时发展到鼎盛。笈多秣菟罗佛像的特点是佛陀螺发右旋,肉髻高圆,双眉之间有白毫,眉毛修长高挑,大眼睑微睁低敛,鼻梁修长挺拔,上唇较薄,下唇稍厚,表情端庄寂静,有超脱典雅之美。着通肩式大衣,极为薄透,紧贴躯干,四肢突显,甚至微妙表现出大衣内裙腰部所系的纽结。
萨尔那特造像在秣菟罗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大衣更加薄透,躯干、四肢更加突显。秣菟罗像尚有装饰性圆绳线,而萨尔那特像通身无一根衣纹,只是浅浅地做出领口、袖口和大衣下摆部,使人感觉到大衣的存在。
博物馆里也展示了不少波罗样式的铜造像。波罗式造像流行于公元8-12世纪,正是密乘(即金刚乘,玄奘大师在那烂陀求学时已感受到了较浓的金刚乘气息)盛行时期。造像在材质上大量使用铜质;造型上一方面恢复了早期笈多造像的典雅风格,面相庄严,体态优美,另一方面受密教影响,造型开始繁复化,装饰繁缛;内容上除了传统的佛和菩萨像外,出现了大量金刚萨埵、明王、度母、黑财神等形象。两种风格的融合形成了这批造像的独特风貌。
但由于年代关系,早期犍陀罗风格的造像在这里的陈列中为数不多。我特别关注犍陀罗造像,因为这是联系印度、中亚和汉传佛教造像最早的一条纽带。
犍陀罗造像发源于古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罗地区(今指以巴基斯坦白沙瓦为中心,西北到阿富汗的哈达,东南到印度河东岸的塔克西拉,北到士瓦特,东西宽200多公里的地区),与早期秣菟罗造像几乎起源于同一时期。萨珊王朝的入侵毁灭了贵霜王朝的统治,整个印度西北地区的寺院和造像都遭到了极大破坏,而犍陀罗造像在其发源地一度黯淡下来。
犍陀罗造像采用古希腊罗马的形式和技巧承载佛教的教义、故事和人物,在相貌和风格上与秣菟罗风格有着显著的差异。前者一般身穿希腊式的披袍,衣褶丰富,多由左肩下垂﹐袒露右肩;人物身材高大,比例匀称,骨架分明,肌肉健硕;面部表情沉静肃穆,有明显的欧洲人特征:高鼻、大眼、薄唇,颐部丰满,额际宽阔,头发自然卷曲,通常有宽大而鲜明的顶髻。因此艺术界惯于称其为希腊式佛教艺术。
佛教传入犍陀罗,最早不过公元前3世纪中叶。当时阿育王向四方派遣了许多传教使团,其中末田地被派赴罽宾和犍陀罗。而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王帝国亚历山大大帝远征印度,地中海文化在印度西北部落地。两地雕塑艺术的互相激荡和碰撞,最后融合在了犍陀罗地区,犹如当年罗马攻占希腊,而反被希腊的艺术精神所浸染。佛教及印度文化作为母体,希腊及地中海文化则是推动的力量,最终形成了犍陀罗风格。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必定会突破旧有的躯壳,向外扩散与其他文化接触。随着佛教向北、向东的传播,犍陀罗造像的风格行走于中亚和东亚地区。虽也入乡随俗,其外貌随时、随地而变化,但基本特征与精神仍在,一眼便能与其他风格区别开来。
最初的犍陀罗雕塑家常使用佛本生故事和佛传题材进行实际创作,直到成熟期,佛和菩萨造像才开始丰富起来。通常表现了佛陀三十二相中较为明显的相好,如发髻、肢体等特征,其他不易用雕塑手段表现的相好则在不违背通常习惯的前提下略加展现,如鹅王蹼相、丈光相、白毫相等,表现得如同装饰一般。比起佛像的庄严,菩萨造像则显得富于世俗特色,穿着和打扮都和现实生活无异,一说是为了体现菩萨救拔众生的慈悲,所以才塑造得平易近人,一说是融入了希腊文化中人格神的理解。
尽管我们可以从这些作品中看出外来的因素,但这些元素最终还是汇归于印度式的范畴。虽然犍陀罗造像的地位和影响如此重要,但对此的确认直到一百多年前才完成,原因很简单:公元5世纪下半叶,印度西北部遭到不信佛教的嚈哒人(Hephthalites)的大举侵 略,犍陀罗本土佛教寺院被全部焚毁,劫后残存的佛教石雕又以各种原因被埋藏地下,直到英国统治印度时期,这批艺术珍品才重见天日。
犍陀罗风格的走向就像佛教本身,虽然在源头凋敝,但却深刻地影响了中亚地区、中国西北及中原的佛教石窟及造像。犍陀罗式不仅仅是一个艺术概念,更是佛教北传和东传的一个折射点。人们在谈到中国佛教石窟造像时往往直接溯源印度本土特色的造像,就如同一提到佛教就要回归印度,一提到佛经翻译就直追梵本,意欲正本清源,却容易忽略文化的传播和传承所经历的漫长而广阔的时空中亚和西域。站在那烂陀寺精美绝伦的造像前,心中自然浮现出沿着玄奘大师西行之路行进,沿途所见大小石窟中的珍贵造像。探寻印度佛教造像与汉传造像间深刻而古老的渊源是我的心愿和责任。
犍陀罗造像传入中国走的是丝绸之路,在越过葱岭后,往北经由疏勒,传至龟兹、高昌等地,向南经过莎车,传至于阗、米兰等地。北线重镇龟兹是西域的文化要地,龟兹石窟造像群则是北线上最耀眼的明珠。它东至焉耆境内的锡克沁明屋,包括吐鲁番的吐峪沟石窟,西至疏勒境内的三仙洞石窟,东西绵延千里,而以克孜尔石窟最为著名。
人们发现,克孜尔洞窟造像与巴米扬地区的洞窟有着较多联系,因此猜测龟兹造像中的犍陀罗风格实际上来源于阿富汗地区,而非直承犍陀罗。其实犍陀罗造像到达中国西域的时间与到达阿富汗几乎同时,巴米扬石窟群和龟兹石窟群为同一时期开凿,而且两地交通往来甚多,并不能绝对地判定其源流先后。佛像离开犍陀罗,在东传过程中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根据不同地区的信仰需求衍生出不同的形式,比如洞窟形制的演变和窟中壁画的产生,这在龟兹和巴米扬的洞窟中都有体现,这种相似有时是佛教在地区间传播的一种相互印证。当然,阿富汗地区的造像确实对中原造像有不小影响,比如犍陀罗风格在梵衍那国(巴米扬)附近的迦毕试国发展出表现神变的焰肩佛(双肩上生火焰)、足下生水及背光中有火焰的特点等。
龟兹造像对传来的风格没有简单照搬和模仿,而是形成了鲜明的龟兹特色,虽然我们不难在其中找到犍陀罗的风范。有的壁画上可以看到这样的佛脸:长脸,半睁的长眼,脸上涂白,白毫涂以红色,眼、睫毛、眉毛、头发用黑色表现,眼窝边缘和鼻翼等用茶色线描。柔美的女性特征逐渐融入造像,早期犍陀罗造像面部的髭须和健硕有力的男性风格在龟兹渐渐淡化。而展现佛本生故事的菱格画的出现,更是龟兹造像的一大特色。从石窟形制看,克孜尔窟的中心柱窟、大像窟虽与印度和阿富汗相似,但也生发出新的特点,并在未来影响到中原地区的石窟。可以说,龟兹石窟群是造像东传的重要中转站。
相对于龟兹,丝路南线于阗地区的造像对犍陀罗的继承更为直接。佛像东传在西域经历了复杂的演变,佛法的传播保证了对印度传统的保留,文化的接触形成了独特的地域特色。龟兹的发展和于阗的传承沿着丝路东行,最终在古凉州地区汇合,犍陀罗风格便在这不断的丰富和演变中又东进了一步。
凉州石窟,是指以武威天梯山石窟为代表的诸石窟。考古学家宿白先生把凉州造像称为凉州模式。史***载,河西地区的佛教首先受到中原的影响,此后由于北凉统领沮渠蒙逊崇佛,西域的佛法由此广泛进入凉州地区,佛教造像也随之而来,以姑臧(即武威)为中心四向传播,后来的敦煌、麦积山和炳灵寺石窟都在影响之内。沮渠蒙逊尤其重视在山崖上凿造大型石窟,加上凉州地区重视禅修,所以石窟兴盛。在凉州地区的天梯山、肃南金塔寺、酒泉文殊山千佛洞等窟中所见的释迦牟尼佛、交脚弥勒像、供养人壁画以及部分中心柱窟顶的大型飞天等都能找到龟兹造像的风格;而在于阗寺院流行的千佛也出现于凉州石窟,可见新疆地区的石窟造像对凉州造像影响甚深。
凉州造像向东影响了云冈石窟,向西影响了敦煌石窟群。昙耀五窟造像是云冈的代表作,曾有人笼统地将其说成是印度风格的发展,并且受到了敦煌的影响,后来通过更深入的研究才发现云冈大佛的源头在凉州。在云冈石窟中可以看到印度、西域和凉州石窟的各种特点,比如昙曜五窟的第16窟大佛、第18窟大佛及胁侍的袈裟与秣菟罗风格的通肩袈裟接近,而20窟的露天大佛与犍陀罗风格接近,而且诸多洞窟有印度及阿富汗地区石窟形制的特点。
敦煌群窟的开凿比凉州石窟略晚。北凉衰落后,敦煌在北魏时期成为河西佛教的中心。以莫高窟为中心的敦煌窟群从东、西两方汲取营养,形成独特的风格,成为凉州石窟后又一承前启后的造像群典范。敦煌莫高窟多有来自西域的中心柱窟,早期壁画承袭克孜尔的人物晕染法,这些都是西域风格的反映。但石窟形制中又加入了汉地的元素,克孜尔壁画中裸露的天人伎乐都穿上了衣服,菩萨造像的女性化比龟兹造像更甚。
虽说云冈和敦煌造像直接延续的是凉州模式,但印度、中亚和西域的造像特点比比皆是,而这些特点又受到了汉地风格的影响,说明造像在东传过程中经过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各种风格被不同程度地运用和改造,并在这两处石窟中较为集中地体现出来。
佛像自犍陀罗出发,进入西域,经过河西走廊传到中原及北方地区,走过了一条保留与演变之路。人们多认为这是一个逐渐汉化和世俗化的过程,犍陀罗和印度的风格逐渐淡去,汉地的特征日渐明显,世俗化意味也进一步融入造像中。从艺术风格和手法上来看,这是显见的。但根本而言,这些变化以佛教东传并逐渐为汉文化接受为背景,体现了人们内在的信仰需求。佛教造像绝不是纯粹的艺术创作,其宗教价值始终是第一位的。虽然在造像中不断加入世俗化的元素,表面上是反映生活,但终究是对世俗的超越。比如早期印度洞窟没有壁画,而在中亚、西域和中原地区的石窟中出现了众多精美的壁画。壁画上大量的人物、山水、景观、楼宇等都与日常所见不同,意在引夺众生的烦恼,反映佛教清净名言中的意境,是佛教世界观统理造像的体现。壁画的出现,绘塑的结合,丰富了表现手段,更好地烘托了宗教气氛。
无论风格、表现方式和艺术手法如何变化,造像的源头都是优填王为迎接佛陀而塑造的牛头旃檀佛像[1]。自此首尊佛像问世,佛弟子们对佛陀的礼拜从敬塔逐渐转移到佛像上,石窟的用途也从修行转为了礼拜。无论是印度还是其它国家和地区的佛弟子,都希望能够塑造出与佛陀最为接近的佛像。因此最初总是尽可能遵循佛教源头传来的风格来塑造佛像;在没有条件遵循的时候就根据当地传统来造像,这是佛像体现出不同风格和地域特色的主要原因;发展到更晚时期,则根据印度传来的经典造像法度进行创作。不仅古人造像有如此心理,直到明清时代依然如此。这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过程,虽然恭敬心尚存,但佛像的失真与信仰潮流的向后演进是一种必然。人们因此离佛陀越来越远,也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要讨论诸大石窟造像传承的源流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们不仅承载了不同时期人们对佛教的信仰和不同理解,也经受了不同时期复杂的政治、文化等因素的洗礼。在敦煌莫高窟和安西县东千佛洞,我有幸见到了传说中的双头佛壁画。双头佛源自佛经故事,西夏黑水城曾有一尊珍贵的泥塑双头佛像,后被俄罗斯人窃取,现存俄罗斯博物馆。据说四川巴中摩崖造像群83号龛三佛的中间佛亦为双头,袈裟反披,偏袒左肩。双头佛造像为什么频频出现在古代丝绸之路上,这是一个亟需研究的问题。《大藏经》对此记载绝少,但在其他未入藏经的文献中尚有记载。我想这依然与文明的接触有关。丝绸之路是诸多文明交汇处,也曾是佛教兴盛之地,必然有许多中原佛教格局中见不到的人和事,只是它们被时空掩藏了。偶有浮出地面者,就显得弥足珍贵,堪为奇迹。我想双头佛就是其中一例。
佛像的传播也好,佛经的传译也好,佛教的弘传不仅是宗教行为,也是一种文明的广布。在对世界文明产生作用的诸多力量中,信仰的力量是最强大、最持久也是最富生命力的。而在各种信仰的力量中,又属佛教的信仰真正契合人类对文明的理想。文明史上,当人们以冲突与暴力完成文明碰撞的时候,佛教以一种决然和平,超然物外的姿态完成了这件大事。这种看似平和却无比坚韧的力量,哪怕是在灰飞烟灭之后,依然给世人留下不可磨灭的财富。这是佛教的伟大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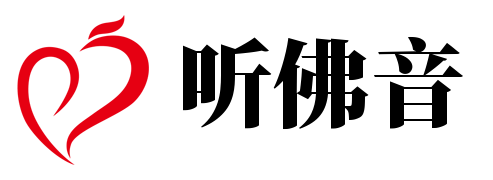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