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远:佛门一粒米
佛门一粒米
王志远
1994年春节的前一天,我和妻儿一同从北京赶到厦门。对鹭岛的厦门虽闻名已久,却还是第一次飞临。与北方相比,这里的春节少了些冬去春来的意味。在我的眼里,青山依旧绿,绿水依旧长,和风徐徐,已知北京四、五月时的模样。只是傍晚有些寒意,但也不过略似十月的秋凉。
我来参加南普陀寺的一次盛会。盛会有两项内容,一是庆祝禅堂落成,二是南怀瑾先生将来新禅堂里为大众讲七天课。而主持这两件大事的,都是方丈妙湛大和尚。
我没见过妙湛法师,仅仅知道他最重文化最重教育,是佛教界中以文化和教育推动佛法弘,传的大师。我想,他或许就像一位学者吧?
除夕之夜,我被请到斋堂。这里是平时僧众共进斋饭的地方,在这辞旧岁、迎新年的夜晚,成了全寺上下同度佳节的会场。走过周围坐满了僧人的一桌一桌的摆放着糖果、瓜子和水果的节日“茶筵”,我被一直迎到最里面、最上首的一桌旁,在左手处落座。
在这一桌主座上,一位长者泰然而坐。他的面庞方中略圆,慈眉善目。上眼皮由于年老而松弛,然而两点炯炯的目光却像黑夜里的星斗一样,似乎不经意地闪着光芒,反倒射入了仰望者的心田。他并不像什么满腹经纶、踌躇满志的学者,他只像一位慈祥睿智的老人,但我已经一下子就认定了,他老人家一定是妙湛法师。
老人向我微微颔首,嘴角挂上一丝笑意。他没讲什么,连一个字也没讲,然而,我却感到心里是那么充实、那么亲切,仿佛他已讲了许多,仿佛我们已相识许久。
除夕的茶话在进行。始终是妙老做“开示”。大约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妙老一直在讲。我坐在那里细细地听,渐渐发菩提心现他竟然是在重复几乎相同的一段话。我不禁一惊。而更使我自己吃惊的是,这几乎相同的不断重复的话,竟然像陈酿的老酒一样,使我激动,使我深思,使我终生难忘。
妙老反反复复地讲一句偈语:
佛门一粒米,大如须弥山。
此生不修行,披毛戴角还。
妙老讲的是出家人要珍惜大众的供养,哪怕是一粒米,也要看得比须弥山还大、还重。对大众供养的最好报答,是竭尽一生的刻苦修行。如果只享用而不修行,下辈子免不了要变马变牛去偿还。
在并不明亮的灯光下,在穿着深赭色、黑褐色僧装长袍的僧众的围坐中,只我这一个白衣人,聆听一位佛教大师对教内徒众的训诲。我突然感到心头的沉重。
我常常见到的,是信众虔诚的敬养,是僧众的坦然的受纳。我何曾想到过,一位德高望重的佛教大师,在除夕喜庆的夜晚,却语重心长地讲着这样一个回报众生的严肃话题。仅仅是能想到提到,已经足以令人感动了,更何况他是那样诚恳、那样认真。他不是说给别人看的。他几乎是在喃喃自语,仿佛一位慈母在除夕的灯下向儿孙们述说着自己一生的做人准则。
如果每一位中国的僧人都这样想、这样做,中国佛教会是什么样子呢?如果每一位中国人都有这样想、这样做,中国又会是什么样子呢?古人做官时,为了提醒自己,竟能写出“尔食尔禄,民脂民膏”的警语,高悬在座右,其高风节、悲悯情怀,难道不正与佛家相表里么?
我敬重佛门,还不止于此。妙老偈语中的后两句,鲜明地体现了佛教的因果观。我推崇建立因果观的任何努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这样的信念中,有一种正义的力量。一个公平的社会,一定要有正常的因果关系。因果颠倒了,社会必然混乱;社会的不公道,必然是由于种瓜的得了豆,种豆的得了瓜。正是有了因果观,佛门之人才不畏果而畏因,坚信造善因而必得善果。“已作不失,未作不得。”既存善恶终有报的信念,便能安分守己、不作非非想。如果有什么人还想说这也是迷信的话,我祝愿他死后得到机遇变成一只老狐狸,以便终有一天能去忏悔。
在我的印象中,妙老头上和身后是光是越来越明亮了。或许那只是因为我心中的一切念头都涌向了那里。这记忆并没有随着岁月流失,反倒愈来愈清晰。
除夕之后,我只见了妙老两面。
一次是我去向南怀瑾先生辞行。由于事先不相识,又无缘相通,我没有得到听课的席位。所经,初次见面也成了初次别离。先生离座还礼,反倒使我受宠若惊。当然,也正因有此一面之缘,此后我才得以屡受南老师恩惠。
使我难忘的,是看到妙老端坐在讲台左侧。宽容、大度、庄严、肃穆。他似乎在听南老师和我说话,又似乎在看着满堂的打坐人。他置身在数百众之中,却仿佛已面对着白云流水。我想起那天登五老峰归来写就的
“登山望海歌”
登上高山,遥望大海,
波光粼粼,明明就在眼前,
其实不在天边。耳旁又响起
海潮的絮语,其实是山风吹过心间。
从厦门回到北京后,我曾在《佛教文化》期刊上写道:“祝贺妙湛大和尚主持禅堂初讲,广开言路,功德无量。并为参加禅堂落成典礼所受之礼遇再致谢忱。
贺诗谨奉:“
稳坐山气派,弘传海胸怀。
南天擎一柱,只眼大道天。”
诗中写到的山与海,一柱和只眼,都是我在禅堂里那一瞬间感受到的。
另一次见到妙老,是妙老特意在方丈楼为我送行。这一次得以和妙老亲近,谈了不少发展佛教文化的构想。妙老诚心诚意地约我来南普陀讲课,我感到十分荣幸。妙老讲话是东北口音,在南海佛国里听到这么淳朴的语调,备觉亲切。
我毕竟是要走了,尽管和妙老还有不少话要唠唠,但想的是还会来。妙老却比我更珍惜这会面。或许我那时还是年轻了些,一步步走下楼来,没有太多的犹豫。直到走下楼才发现妙老也随之送下楼,直到走出门才发现妙老也随之送出门,直到走开了几十米,当我恋恋地回首一望时,才发现妙老他老人家仍站在楼前,一位八十多岁的风烛残年的长者,手臂倚着年轻的侍者,依旧望着我。
我心头一热,双眼忽然模糊起来。我禁不住回过身去,遥遥地,向着老人家深深一鞠。几滴热泪,禁不住洒在南普陀的净土上。
妙老到北京治病,我知已晚。他刚刚离去,留下了“勿忘世上苦人多”的遗言。
去年秋天,一位朋友从南方归来,说有极珍重的宝物赠我。自锦盒中取出,方知竟是妙老的一枚舍利,一枚小米大小的略有点微红色的舍利子,静静地躺在一尊大约30公分高的透明的小宝塔里。朋友从来未听我讲过我与妙老的深情,也没有人对他说过我对妙老的思念,但他却将妙老的舍利子捧到了我的面前。
妙老,是您也思念着我吧?
妙老,我眼前这一粒圣洁的米,我心上那一座崇高的山。
1997年11月11日子夜2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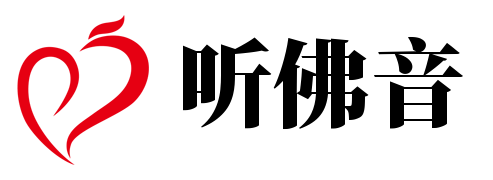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