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子里风雅 焚香品香
文人士大夫的焚香品香,风雅渗透到骨子里面,品香与斗茶、插花、赏画同为贵族精神生活追求的极致,这是一种结合了财富和学养的文化生活方式。
焚香,成为文人雅士一种根深蒂固的生活习惯,须臾不可离。明代文震亨《长物志》描述焚香情形:于日坐几上,置倭台几方大者一,上置炉,香合大者一,置生熟香;小者二,置沉香、香饼之类;瓶一。斋中不可用二炉,不可置于挨画桌上,及瓶盒对列。夏日宜用瓷炉,冬日用铜炉。可见焚香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里也可看到文人对沉香用具的讲究以及沉香品类的多样化。
宋代许多词人骚客以沉香入诗,在更早的时候,也有不少诗人把沉香写入诗中。譬如唐代就有李白、白居易、罗隐等诗人与沉香结缘。
李白的杨叛儿》吟道:
君歌杨叛儿,妾劝新丰酒。
何许最关人?乌啼白门柳。
乌啼隐杨花,君醉留妾家。
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
《杨叛儿》本来是北齐时童谣,李白借用为诗名,抒发自己的情感。青年男女,唱歌、劝酒,诗中的白门,本是刘宋都城建康(今南京)城门,是男女欢会之地的代称。最牵动人心的是白门柳,醉而留宿,充满柔情蜜意的陶醉。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博山炉是一种炉盖作重叠山形的熏炉。名贵的沉香,在博山炉中缓缓熏烧,慢慢释放,在沉香的作用下,爱情的升华到达顶点,仿佛那香火化成烟。前人诗句君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将沉香与香炉的关系直接比作了爱情的双方,带有双重的象征意味,沉香直接镶嵌在人们的生命和爱情中。
罗隐的绝句《香》,有沉水良材食柏珍,博山炉暖玉楼春的名句,也点明沉香和香炉的关系。可见在唐代,诗人们对沉香不吝赞誉,说它是良材,因在博山炉中熏烧,呈现出春意盎然的意境。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晚年曾举行一次集会,地点在其洛阳香山居室庭院,参与雅集的人物都是一时俊彦,有怀州司马胡杲、卫尉卿吉皎、前观武军长史郑据、慈州刺史刘真、御史卢贞、永州刺史张浑等人,一共是九位老者,称香山九老。九老到了晚年,感慨既多,而心境也相对平静,他们在这次聚会上咏诗、作画、焚香。此前,白居易在他的诗歌《宫词》中写道:泪尽罗巾梦不成,夜深前殿按歌声。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熏笼坐到明。独坐愁城的时分里,熏香的香笼一直陪伴着他。可见品香与其意志、思维相始终。
香山九老的雅集在以后成为艺术家常常表现的题材,宋、明、清几代都有画家、雕塑家来表现。近代的林纾先生就作有《香山九老图》,现仍存世。
唐末诗人欧阳炯的《禅月大师应梦罗汉歌》由衷地写道:西岳高僧名贯休,高情峭拔凌清秋。天教水墨画罗汉,魁岸古容生笔头闭目焚香坐禅室。或然梦里见真仪,脱下袈裟点神笔。高握节腕当空掷诗名画手皆奇绝,觑你凡人事事精
欧阳炯是晚唐文艺名家,益州(今四川成都)人,在后蜀任职为中书舍人。随孟昶降宋后,授散骑常侍,工诗文,特别长于词,又善长笛,是花间派重要作家。他赞扬贯休的画意之高,有一个细节,就是闭目焚香坐禅室,在动笔之前,只需闭目焚香坐禅室,构思冥想,一切便成竹在胸了。焚香的作用是前导,也是灵感的积聚。
士大夫酬酢宾客,置酒高会,少不了一番轻歌曼舞。苏东坡在杭州时节,曾参与西湖宴会,他在词中写道:石榴半吐红巾蹙。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浓艳一枝细看取,芳心干重似束在这样的场合,沉香之熏腾,乃是友朋之间酬酢的重要仪注。
沉香是情景、心情的补充,也是词情婉丽的催化。换句话说,是他们的感受生成为作品过程中的桥梁和媒介。
沉香虽然常常烧熏于教坊优伶之间,但最终结果,尤其在宋代,却升华为士大夫的知识分子精神领域所专有了。也就是说,它是交际对不可或缺之物,促成其变化自然,浑然天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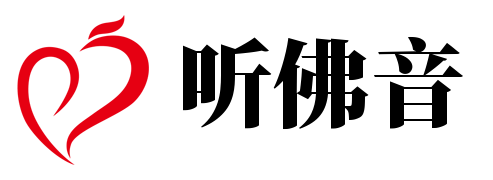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