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成就者之歌》祖古·乌金仁波切 第三部 第四章
讲述:祖古·乌金仁波切
记录整理:艾瑞克·贝玛·昆桑 马西亚·宾德·舒密特
翻译:杨书婷 郭淑清
第四章 拉萨令人称奇的大师们
宗萨·钦哲在拉萨的时候,我得以和一位绝妙的大师,也就是深受喜爱的宗萨·钦哲共度时光。在康区,这位转世祖古与伟大的钦哲本人同享盛名;他不只是第一世钦哲的祖古,几乎就是他本人;他是个博学、高贵的大成就者,同时具有令人赞叹的仪表。他后半生的时候,生了一场重病,而且拖延了三年,一直找不到治愈的疗方。最后,他受请求迎纳一位佛母来改善健康状况。他答复道:“如果都没有办法的话,我将归还我的比丘戒。”他随即描述了一个特定的年轻女性及其下落。而后,她和她的家人收到了一封邀请信函,她就来与他同住了(1)。宗萨·钦哲舍戒不再是个僧人,而成为一位瑜伽士,而且是位圆满的瑜伽士。当康区的动荡时局变得不堪一击时,他以短程旅行为借口,在没有任何人知道的情况下动身前往中藏,这样一来也就不会有人阻止他了。途中他经过了囊谦。就如我所提过的,宗萨·钦哲先前曾造访桑天·嘉措的隐修处垒峰。在那里,宗萨·钦哲请求我的上师给予他《新伏藏》法中,由第十五世噶玛巴所撰写的部分,那是他未曾领受过的传承。不过,当时我并未见到他。有一天,当我碰巧在拉萨大昭寺里参拜释迦牟尼佛雕像的时候,有消息说宗萨·钦哲也来了;他气度宏伟地迈着大步走进来,头上戴着莲花生大士著名的莲花冠,身上穿着法袍。(2)四周的人都在窃窃私语:“看那边!那是谁?看起来是位伟大的大师。他的穿着就像莲花生大士一样。”他几乎马上就成为全拉萨知名的人物。当他待在一位举足轻重的权贵家中时,我去探访他,当时他正在传授《心要四支》(FourBranchesofHeartEssence),那是大圆满中最重要的一套法教。“你是谁?”他问道。“我是个康巴人。”我答道。“来自康区什么地方呢?”“我来自秋吉·林巴的家族。我是他的曾孙。”“涅琼·秋林没有孩子。”宗萨·钦哲与涅琼的秋林非常亲近。他继续说道:“那么你是谁的儿子呢?”“涅琼·秋林是转世,而我是秋吉·林巴本人的后代子孙,因为我父亲是由尊者的女儿所生的。”“噢……所以也许你是大家都在谈论的那位秋吉·林巴的后代子孙,也就是给予噶玛巴利培·多杰《三部》灌顶的那位!那是你吗?”我除了说“是的,那就是我”之外,还能说什么呢?我猜,这表示我们已经正式认识彼此了。“好,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必须为我安排和噶玛巴见面。”他说:“他持有一种灌顶的传承,能让弟子精熟于觉知的展现(3)。我必须从利培·多杰本人那儿领受它。请你协助我,代我请求他。”为了协助促成这样的吉祥会面,我首先带着噶玛巴的秘书长与噶玛巴家族的几位成员去见宗萨·钦哲。这次会面进行很顺利,很快地,宗萨·钦哲就受邀至楚布寺给予教授与灌顶。我清楚记得宗萨·钦哲在廿三日抵达后,就一直待在楚布寺,直到次月的八日才离开。我们如意宝怀着极大的敬意对待宗萨·钦哲,安排他在最好的寮房中。我非常幸运地能从他们两位那儿领受灌顶,并亲眼目睹他们彼此喜爱对方。新年庆典期间,宗萨·钦哲待在楚布寺,受到极大荣耀的款待,并被安排坐在崇高的法座上。噶玛巴与宗萨·钦哲噶玛巴私下告诉我:“我对于能够款待这样一位伟大的上师感到激动不已。尽管当前是多事之秋,他却让我感到全然的安心。”噶玛巴请求了一部第一世钦哲的心意伏藏,那是一部具有秘密封印形式的《长寿佛母墙达利》法(4)。接着,宗萨·钦哲也请求了红观音菩萨的灌顶,称为《天人师之洋》(OceanofConquerors),这是从第二世噶玛巴噶玛·帕师(KarmaPakshi)时代以后,每位噶玛巴最重要的一个本尊。噶玛巴也给了他和这个灌顶相关的一个特定面向,称为‘展现觉智的灌顶’(empowermentforplayofawareness)(5)。而在这些灌顶期间,只有噶玛巴的弟弟朋罗仁波切(PonlopRinpoche)和我被准许待在内室里。”灌顶结束后,谈话内容转到了西藏的未来。宗萨·钦哲说道:“在我看来,西藏局势极度恶化。事实上,我来此地主要原因是为了亲自向您请示,您对我到贝玛古去的看法。”这是位于印度边界一处非常偏远的山区。过了一会儿,噶玛巴说道:“贝玛古、贝玛古……看起来并不好;山群非常陡峭,路上的河川也难以跨越,而且,到最后局势动荡也会影响到那里。那是我所见到的。仁波切,你必须到锡金去。”“很好,如意宝,我有信心您是个能清楚见到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我将依循您的忠告。我原本是计划要由贡波区离开西藏,但我却有所疑惑。那是我为何来请示您的原因。”宗萨·钦哲待在楚布寺期间,成了我的老师之一。从那时起,我得以向他澄清许多重要的疑点,因为一连好几天,一些自命不凡的楚布寺秘书禁止他去见噶玛巴。这并非新鲜事,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其他许多伟大的上师身上。此外,当宗萨·钦哲初次抵达楚布寺时,似乎没有人赞赏他确实是个何等超凡、伟大的上师;除了我之外,没有任何人来向他请求法教。有个原因是,他住在噶玛巴的寮房里,让人难以进入;另一个原因则是,噶玛巴身边的人似乎丧失了对其他喇嘛的赞赏之情;他们发现要对任何人产生信心并不容易。因此,我何其有幸,在那段期间没有人跟我争着要见宗萨·钦哲。但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曾为上一世噶玛巴佛母的楚布·康卓(TsurphuKhandro)、楚布寺的金刚上师,还有我,都被人看到进进出出地要取得法教。到最后消息传开了,很快地,人们就站着排队要见他了。离开楚布寺之前,宗萨·钦哲请求八套中等长度的《圆珠巴昆色》仪轨,他说:“这是一部专门针对这个时代的特别仪轨。请向我们如意宝询问,我是否能得到它的几本复本。”接着,宗萨·钦哲要求借用一尊小雕像,那是由第一世噶玛巴在青铜上咬一口来开光的。这些雕像在康区从未被人见过,不过宗萨·钦哲知道噶玛巴有几尊这样的雕像。对于这项请求,噶玛巴似乎相当高兴,因此他要人去搜寻他存放圣物的地方,且找到了两尊雕像。“我想给你一尊。”他突然这样告诉宗萨·钦哲。宗萨·钦哲试图拒绝,噶玛巴却强迫他收下。你应该瞧瞧这件事在整个楚布寺所引起的骚动。每当两名僧侣在路上相遇时,谈话的主要话题就是,“这位来自宗萨寺的萨迦喇嘛得到了我们最珍贵的宝物之一——我们第一世噶玛巴杜松·虔巴(DusumKhyenpa)咬过的雕像。倘若我们如意宝就那样把宝物送人的话,我不知道佛法将会发生什么事!他把我们的心爱宝贝送给了人。”全寺弥漫着一股批判的气氛。我试图阻止僧众,告诉他们说:“别用那种态度说话!噶玛巴是佛法之主,如果他以那种方式将雕像送出去,必定有其道理。除此之外,它也不过是两尊中的一尊罢了,另一尊仍在楚布寺。”“没错,没错,尽管如此,两尊仍比一尊好!”这是他们的回答。毫无疑问地,噶玛巴的看法和他们不同。当宗萨·钦哲即将结束他停留的日子,噶玛巴说道:“当这位老喇嘛离开楚布寺后,这地方看起来将会空荡荡的。”珍贵的传承法教当宗萨·钦哲再度回到拉萨时,我得到机会从他那里领受到更多的法教,尤其是他给了伟大米庞所著的一份一般瑜伽士指引(6)。开头是这么写的:“无需长时问研、思与修,依口诀而持心髓,一个凡俗瑜伽士经过微小困难后,也能成就持明者之境界——此乃甚深之道的威力。”他用了几天时间,每天一大早以极为缓慢的步调给予教授,而我非常享受我们一起上课的时光。我们也有机会交换其他法教,举例来说,我带了噶美堪布针对《七支深密轮》(SenfoldCycheofprofundity)中,关于莲花空行母(LotusDakini)修持的一些阐释。宗萨·钦哲做了一份复本,而我也乐意给予他口传。当我在拉萨的时候,也见到了顶果·钦哲,他是伟大钦哲的另一位转世。虽然我曾听过他,而他也揭示了我送给德喜叔叔的那张羊皮纸空行卷轴内容,但我却从未见过他。刚好,德喜叔叔已经在那个冬天往生了,他有一些特别的私人物品要送给顶果·钦哲,而我则身负将它们带去桑耶寺交给顶果·钦哲的任务。顶果·钦哲身材高大且相貌出众。他告诉我关于他透过德喜叔叔与我的家族结上法缘的事,并说他乐意给予我一些灌顶。就在那时候,他正要到楚布寺去见噶玛巴,所以他说等他回来后,我们再进一步讨论。我利用这个机会提醒他,德喜叔叔告诉我关于《八佛母》(EightConsorts)空行伏藏的故事,并补充说到德喜叔叔命令我向这位钦哲祖古请求这个传承的事。顶果·钦哲回答:“回到康区后,我把那四十页内容拿给宗萨·哲钦看。他告诉我说:‘你必须给我那部法的灌顶与口传。我之前已发觉到秋吉·林巴空行母系统的教授中,有一部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写下来,这个看来似乎正是那部教授。你做得好极了!’我于是将整部系统的灌顶与口传献给了他。”“至于你的请求,目前我们运气不好,因为我将法本留在他那里,所以我现在无法把法教传给你。将来你见到宗萨·钦哲时,你必须向他请法,他说他想负责那部法教。”尽管如此,顶果·钦哲对于我请求这部法,看起来似乎感到相当开心,对我非常地仁慈。“这是一部庄严宏大的伏藏法,”他继续说道:“但我能怎么办?我将它送给了宗萨·钦哲,因此我没有法本。由于东藏的情势每况愈下,因此我必须逃到拉萨,却不晓得宗萨·钦哲已经在这儿了。我原本预期他更晚一点才会来。宗萨·钦哲告诉我,他派人到康区收拾那些典籍,不过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所以,过了一段时间后,在我与宗萨·钦哲多次美好的谈话中,有一次我告诉他德喜叔叔所说,关于顶果·钦哲抄录下的伏藏法故事。“仁波切,”我问道:“他告诉我,您有经文。您有带在身边吗?”宗萨·钦哲回答:“祖古所写下来的这部伏藏法,绝不是普通的伏藏法!他捕捉到相当了不起的内容、甚至包含了一部密续。我告诉你,那可不是所有伏藏师都能办得到的!伟大的钦哲与康楚可以办得到,而秋吉·林巴也得到了几部。”(7)“我迫使罗索·达瓦把这个传承让给我,之后并立刻将整部经文制成木刻板,打算将它传播出去。不过,看看现在发生了什么事!佛陀法教的敌人突然从东方崛起,***已经开始。由于我必须在这么仓促的情况下离开,因此无法将它带在身边。让我告诉你,我设法带出来的东西很少很少——只有三尊小古察雕像;这是莲师为了西藏的利益而将它们封藏起来,以作为他的代表。(8)就这样而已!其他所有的神圣图像、雕像和圣骸,我根本没有任何机会带出来,我们神圣崇高的典籍就这样沦落入佛法反对者手中了!”简单的说,即使宗萨·钦哲保全了那部传承,现在也无法将它传授下去。他也失去了所有代表成佛者身、语、意的神圣物品。(9)因此,当谈到要领受德喜叔叔所建议的这部伏藏法时,我觉得我已经尽我所能,首先向德喜叔叔本人,接着向顶果·钦哲,最后向宗萨·钦哲请法。有一天,宗萨·钦哲说道:“我即将要到中藏一带朝圣,如果你一起同行,我有一些灌顶与口传可以与你分享。也有几部《新伏藏》里罕见的作品我还未领受过,而我想你有。难道你不觉得,如果我们能一块儿旅行一小段时间,会是个好主意吗?你何不请求噶玛巴的允许,跟我一道走?”但事情的结果并未如我们原先所计划,因为那段日子噶玛巴想要修些特定的仪式,而我们也正在修一种与狮面空行母(Lion-facedDakini)有关,需要九天时间的除魔仪式。因此当我告诉宗萨·钦哲说,噶玛巴不让我走的时候,他别无选择,只好在没有我同行之下离开了。
敦珠仁波切我已经提过敦珠仁波切,不过从来没有说明我们见面的情况。当宗萨·钦哲还在拉萨的进候,有一天我去见他。不过,到了门口时,我才被告知他那天不在;他已经到拉萨近郊的一处帐篷营地,去请求敦珠仁波切授予一个灌顶。当我下次见到他时,他表露了对于敦珠的深切赞赏:“在我们当前这个时代,我不相信有任何一位持明者比敦珠还要有成就。那是为何我必须向他请求灌顶的原因!”不久之后,我自己遇见了敦珠仁波切,他正待在我所认识的一位好性情的贵族家里。当时这位显贵想在家中的寺庙修十万遍会供,所以邀请敦珠仁波切前来主法。这位显贵知道我在镇上,所以也邀请我来。我和敦珠就是在这十万遍会供期间相遇,也相处了一些时光。“你是谁?”他问我。“我是从康区来的。”我回答道。“你从康区哪个地方来的呢?”“从囊谦来的。”“你属于哪个传承呢?”“我属于巴戎噶举。”“你修什么法呢?”“我修持秋吉·林巴的伏藏法。”“那么,你也许和他有亲戚关系。”“是的,实际上,我是他曾孙之一。”“说明一下你的族系。”我告诉他,我是吉美·多杰的儿子,也是桑天·嘉措的侄子。“噢!真的!”敦珠答道:“我从桑天·嘉措那儿领受了部分的《大圆满三部》,并将他视为我的根本上师之一。我最近听说有个康巴喇嘛在楚布寺给了噶玛巴《三部》的灌顶——那个人是你吗?”显然,耳语已经传遍各处了,因此我承认:“是的,那个人是我。”“你有把书带在身边吗?”“是的,我有,就留在我楚布寺的寮房里。”“你有带圣像吗?”“是的,我也有。”“棒极了,因为你必须将那个教授传给我。我在楚布寺得到前三个灌顶,不过我绝对要得到完整的教授。”由于敦珠仁波切非常坚持,因此我必须立刻派遣我的侍者在噶玛巴远行到拉萨西北方的天湖期间,回到楚布寺拿我的书本和圣像。不久之后,我也必须尽我的绵薄之力,将这个传承献给敦珠。恰扎仁波切的试探当这些灌顶进行了几天之后,我遇见了恰扎仁波切(ChatralRinpoche);他的外貌非常引人注目——身穿质地粗糙的毛料衣服、高耸的鼻子,以及康巴人的言行举止。我们的交谈是这样开始的:“你,喇嘛!你从哪里来?”他粗鲁地质问道。“我从囊谦来的。”“从囊谦哪里来?”“我是秋吉·林巴的后代子孙。”“我曾到慈克寺去,不过我在那里并没有看到你。”“我并没有一直待在慈克寺。”“那你从哪里来?说出来吧!”“秋吉·林巴的女儿贡秋·巴炯有四个儿子,其中之一就是我的父亲。”“嗯……嗯……”我已经听说你应当是涅琼·秋林的侄辈。我在宗萨寺那儿认识他,他到那里去探访宗萨·钦哲,但我从未听说他有个喇嘛侄辈。现在我听说我们的敦珠仁波切正从这一位侄辈那里领受了《三部》的灌顶,但我们都知道,有很多所谓的‘康巴喇嘛’来到中藏,试验他们各式各样的把戏。因此,我好奇你是否也只是另一个这样的人罢了。嗯……。”恰扎仁波切一直瞪着他的大眼睛打量我,“许多康巴喇嘛来这里,给予他们没有传承的灌顶来欺骗人们。”敦珠仁波切就坐在那里,插嘴说道:“是我请求他给予这个传承的。”很快地,他们开始开起一个又一个玩笑。而在这时候,恰扎仁波切带着得意的笑脸转向我,说道:“好吧,我想你终究不是个冒牌货——那么,你可以继续给予他灌顶了。”雪谦·康楚当我准备离开西藏的时候,有一位名为雪谦·康楚的令人赞叹的大师交给了我一封信,要送给已在锡金的宗萨·钦哲。他把信交给我时说道:“如今要说宗萨·钦哲就是老钦哲本人,绝对是合理的。现今人们要在甘托克见到他,似乎很容易,但事实上,这是相当不可思议的。请你将这封信交给他。”对这位大师来说,要如此赞扬任何人是极不寻常的。但后来当我将信交给宗萨·钦哲时,他把信放在头上,并说道:“这封信是来自一个像老康楚本人的人。对你来说,要见到他似乎是很轻易的事,不过那是令人讶异的好运。”他们相互之间,对彼对都有种不寻常的赞赏与净观。雪谦·康楚已经达致了妄念瓦解的境界。臻至这种层次的高贵生命,行为举止常表现出孩童般,十足自然、不造作的模样,完全不会考量社会常规——雪谦·康楚到了晚年的时候,似乎就是那个样子。有一次,当他在拉萨时,一位中藏大臣来探访他。当时拉萨地区的官员全都将头发绑在头上,并饰以金黄色的圣物盒,而瑜伽士通常也将头发用里面装有圣典或圣骸的一个小圣物盒绑起来。尽管这名男子穿着打扮显然像个西藏显贵,雪谦·康楚仍对他说:“喂,瑜伽士,你从哪里来的呢?”“仁波切,嘘!”有人倾身向他轻声说道:“他不是瑜伽士,他是位大臣。”“喔,你是位大臣。”雪谦·康楚脱口说出:“我以为你是个瑜伽士。你从哪里来的呢?”那位大臣感到非常窘迫。在另一个场合中,由政府高官纳波(Ngabo)邀请了敏珠林寺的琼仁波切、雪谦·康楚、顶果·钦哲,以及多位僧人,一起在大昭寺主修一个法会。这些人全都坐在一起。纳波本人并未到场,而是派他的妻子出席;她是一位身份崇高的妇女,被称为拉蔷·古秀(LhachamKusho),即“夫人”之意。由于她是位贵宾,所以当她将装着钱的信封袋连同哈达一起交给琼仁波切时,她也低下了头——不像平常人从喇嘛手上得到加持时那么低,而是只低到额头互相碰触的高度。雪谦·康楚随即用手肘推了推顶果·钦哲,并突然大声叫道:“喂,钦哲,快点!我应当如何应对那位女子呢?我以前从未跟女子的头部相互碰触。”就在这时候,那位女子已经走过来,站在他的正前方。“只要保持安静,并以额头互碰就好了!”顶果·钦哲在他耳边说道。因此,雪谦·康楚弯下腰,以地位平等的人之间相互问候的方式与她额头互碰。接着,她向他献上了哈达,连同一个装着钱的传统信封袋,以作为供养。坐在他隔壁的顶果·钦哲正在接受哈达与供养时,雪廉·康楚已经撕开了他的信封袋往里面瞧——违反所有得体礼节的规矩。他拿出了钱,并以大家都听得到的音量大声说道:“喂,钦哲,瞧瞧我得到了什么!你拿到了多少钱?”我当时并不在场,不过顶果·钦哲亲口告诉了我这则故事,并提醒道:“在公开场合坐他旁边,真是吃不消。”当雪谦·康楚谈到俗事时,常表现得相当孩子气,不过,当他谈到佛法时,他的智慧就像驱除了黑暗的东升旭日般。在拉萨时,我有一次找到机会问他说,他觉得谁是西藏证量最高深的大师。“看看敦珠,”他答复说:“他的眼睛如此明亮有神,几乎就像老鹰一样;在他的眼神中,你可以看见全然开放的觉悟特质。如果要问哪个人具有证量,就是他了。与他相较之下,其他人看起来似乎都颇为迟钝且心不在焉。”“名气响亮的大师竹巴·永津又如何呢?”我接着问道。“他绝对也达到了那个层次;他的心广阔开放,连丝毫无明都没有。”雪谦·康楚回答道,“我听说他甚至都不睡觉。”接着我问他,他所说的证量高深是什么意思。“这是指当你的觉知无所障碍,且无所执著时,你仍敏锐地安住于当下,了然分明于细节之处。”他当时所展现的正是如此。我确信他就是一位证量极高的大师,而且对他怀着深刻的信心。雪谦·康楚的预感尽管中藏仍旧一片平静,康区却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当我还在楚布寺噶玛巴待在一起时,雪谦·康楚也到那里短暂停留。他告诉了我一个预感:“现在,每当我看到暴乱分子时,我的胸口马上就会痛起来。我觉得极不舒服,或许有一天我会被他们带走。”他做了几次这样的评论。有一次我问他:“为何你会被暴乱分子带走?噶玛巴正要把你派到锡金,去当锡金国王的主要上师。我们如意宝已经安排好了,也告诉锡金人说:‘我要把这位喇嘛送到你们那里,当皇室的上师。’”“既然你很快就要离开西藏了,”我问他说:“为什么你认为他们会把你带走?”雪谦·康楚回答:“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过我就是觉得这很可能会发生。”动身前往锡金之前,雪谦·康楚想要造访中藏其他地方。噶玛巴却告诉他说:“别去,你应该继续待在此地。你很快就必须动身,直接前往锡金了。敏珠林寺的主要功德主已经在那里了,你必须与他相连结,你在那里将有圆满的因缘。”但雪谦·康楚却反对道:“我必须先去敏珠林寺;敏珠林寺就像是宁玛传承的基石,我必须造访那里一次。”他们不断地争论,到最后噶玛巴说:“好吧,如果你非去不可的话,我会替你安排一切,并提供侍者。不过,你不能待在那里超过两个星期。之后你就必须直接回到这里,然后到锡金去。”雪谦·康楚允诺在敏珠林寺待两个星期,一天都不会多。遵循噶玛巴的教诫,他只待了两个星期,接着就动身回楚布寺。在回程的路上,雪谦·康楚在一条大河的渡口意外遇见了一群人。真的很凑巧,他们是林桑(Lingsang)家族的成员,在时局动荡的这个时候,来到了中藏。由于这些人是雪谦·康楚在康区的功德主;因为他们的资助,所以雪谦·康楚有义务要为他们修法。因此,他在那条河的岸边逗留了五天。这么做的结果却是一场灾难——暴乱分子赶到了哪里,把雪谦·康楚抓走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去世的,他必定是从中藏被带回东部的德格,因为有人在那里看到他,接着就不知所踪了。这实在是件令人伤心的事,他当时大约只有五十岁。我的顽固与骄傲不幸地,现在我必须再告诉你另一个关于我固执顽强的例子。正当我准备要去锡金时,噶玛巴告诉我说:“首先,待在我的弟子班酿克·阿汀(BanyakAting)位于锡金的庄园一段时间,然后再前往尼泊尔,到位于加德满都山谷博达的大白佛塔去,你应该在旁边兴建一座寺院。”“佛塔里有个人已经答应要给我土地,而我有封来自山谷其中一位统治者的信函,允诺会提供建筑材料。从我应当派个喇嘛去监督这项计划到现在,已经过了六个月,我想你会是负责这项工作的理想人选。”隔天,当我坐在我们如意宝面前时,有个人拿了一叠共八封信函进来。当他将信函一封封交给我时,也告诉我这些信件是要给谁的;每封信都是寄给尼泊尔政府的特定官员,还有一封是要给土地的赞助人,以及一封给尼泊尔马汉扎国王(KingMahendra)的秘书,甚至还有一封是要给印度籍大师古努喇嘛(KhunuLama),请求他来,尽管我怀疑他是否会来。
“恶劣的时刻将会降临西藏这个地方。”噶玛巴说道,“我要你在尼泊尔建立一座寺院。我已经做了准备工作,要将我们一半的雕像、书籍和法器慢慢地送到尼泊尔。不过得要有个地方存放它们,那就是一座寺院。你必须前往那里建立一座寺院。”他继续说道:“我选择你去是有道理的,因为你有能力当我的代表。我将派遣所有必要的侍者与秘书,并赋予你喇嘛的崇高地位。因此,去将你所有的东西打包,往南到尼泊尔边境的吉隆(Kyirong),再从那边到加德满都山谷,并立即着手兴建主要的寺院。建造工作必须品质精良,而且必须在三年内完成。我们必须现在就此达成共识——盲目相信一切会好转,而留连于西藏是没有意义的。”“对不起,如意宝!”我难以置信地说道:“像我这样的人,如何能实现这样的教诫呢?我的学养没那么好,而我既不是个能言善道的老师,长得也并非高大英俊。在我看来,您挑了个最差劲的人选。派我去,不仅是个没有正当理由的惩罚,而且我确信最后结局肯定也会是失败的。”回顾这件事,我忍不住要笑自己的鲁莽无礼。“康区有这么多伟大的噶举寺院,包括色芒寺在内,”我继续说道:“每座寺院都有能干且杰出的喇嘛。您有权力指挥最优秀的人当您的代表,他们也会听从您的指示——那么做是否会更好呢?您所必须做的,只是表达您的心愿,我确信任何人都将依您的吩咐做事。那才是您应该做的事——因为我不可能承担这样的地位。即使我真的去了,也不会有人听命于我,我不可能允诺在三年内盖好寺院。我比较像是个被称为‘喇嘛’,却以人身化现的饿鬼。选择我代表您,将一无所成,并徒然玷污佛法而已。”我随后站起来礼拜了三次,以展现我坚定的决心。“当我这样的人承担高阶佛教大师的地位时,”我补充说道:“将使人们背弃佛法,并导致他们违犯三昧耶。”“用不着你来烦心这种事,这是我的事。”噶玛巴不为所动地回答道:“此外,顺道一提,我认为人们将会对你有信心。”“我并非企图要说您不对,”我抗议道:“但在我看来,您是试图叫一只狗表现得像狮子一样,而我就看不出要如何才能办得到。”“你实在是个顽固的人!”噶玛巴大声说道:“毫无意义的固执。真是遗憾!显然你并不明了这么做对佛陀的法教和众生会有多大的利益。我对你寄予厚望。”“我并不缺少举足轻重,并大吵着要更高位阶与地位的喇嘛;许多人急切地想要去,还会完全照办我所要求你的事。真是可惜!不过别再提了,至少暂时如此。”他是那么说的,不过并没有用,我仍旧不服从他的指示。这个例子彰显了我顽强的骄傲。我现在很懊悔当时没有利用那个机会实现他的心愿,因为他当然是对的;在尼泊尔建造一座寺院,肯定会为众生带来极大的利益。然而我又知道些什么呢?我只不过是个平庸的傻瓜罢了——但当时我却完全坚持自己的判断。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噶玛巴询问道:“反正你准备要去尼泊尔,不是吗?”“为什么这么问?”我问道。“那里有个叫作玛拉提卡(Maratika)的地方,那是你应当去做三年闭关的地方。”“这地方位于何处呢,仁波切?”“距离加德满都山谷不太远。如果在这三年期间,你能在那里修持一些长寿法,你将会有好的成果。”“求求您,别强迫我那样做!”我恳求道:“我当然听过玛拉提卡,那是莲花生大士获得成就的地方。但我如何取得粮食呢?在那里我不认识任何人。求求您别叫我做这件事。”因此,那次我也没服从噶玛巴的心意。噶玛巴说话的方式极不寻常。当他表达他的心意时,听起来经常不太像是建议,反倒像是可能性,是实际会发生的事。尽管如此,我当时显然并没有足够的信心听从他的话。所以,那两次我并没有履行他明确的心意。失落的珍宝每当我思及那段时间所失去的所有珍贵宝藏时,我对自己的愚蠢实在难以置信,尤其是令人赞叹的楚布寺藏书馆书籍;知道那座无价藏书馆后来的遭遇之后,我很懊悔没有为了我前往锡金的旅程,而要求借出几本书。有一本书特别浮现在我的脑海中,那就是噶美堪布加以注解的《知识宝藏》版本;不只因为那本书是以他自己的大字笔墨真迹所写成,也由于他在字里行间插入了他亲自向作者康楚请益的阐释。整部经文加上康楚自己的评论,写满了三大册。在楚布寺时,我请求借出这些书,噶玛巴也同意了。然而当我追查书本时,却早己被闭关指导上师帝亚·珠彭(DilyakDrubpon)借走了。“我已经请求我们如意宝将这些书借给我了,可以请你将它们送过来吗?”我要求道。“我以三宝的名义发誓,我不会这么做!”帝亚·珠彭回应道,“我不会割舍这些书——绝对不会!我告诉你原因,因为噶玛巴老是把人送来我这里来问问题。没有了这些书,我如何能给予适切的回答?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并未广泛研读,只读过《入菩萨行论》与《三戒》(TriplePrecepts)这些基本经文。我并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而这三册书是我所仅有能支持我说法的东西。”“你说是我们如意宝派你来的,那也无济于事,我也是为他工作。你现在来到这里,声称要挖出我的两只眼睛,让我成为瞎子!我对着三宝发誓,我绝不会割舍这些书。”我跟他是很亲密的朋友,所以我能怎么办呢?我无法与他争论,因此我试着从另一个角度跟他说:“你不需要那样紧紧抓着它们不放。噶玛巴真的说了,我只能短时间借阅它们,就让我拿走一小段时间吧。”“不行,我以三宝的名义发誓,你不可能拿到它们!”他坚决地喊叫道。帝亚·珠彭是位真正的禅修者,也是第一流的人物。但是,一旦他誓言“以三宝的名义发誓!”你就没辙了。如果是其他人的话,毫无疑问地,我会请求噶玛巴施加压力。不过,因为我不想让这件事演变成更大的问题,所以就让事情这样过去了,而我就再也没有机会读到那些书了。在楚布寺的时候,有一天,当帝亚一位刚在色拉学院完成辩证法与因明课程的密友兼亲戚走进房间时,我正和他坐在一块儿。帝亚·珠彭是那种比较单纯的禅修者。“你所理解的空性是什么呢?”他的朋友戏弄地问道。“空性非常简单,就是我们所称的大手印和大圆满。”珠彭回答道。“你这个傻子!你不能仅仅以另一个字眼来定义空性;它应当是所有教授的基础,你却无法描述它。你坐在这里,佯装是噶玛巴的助理教师,你这个骗子!”“好啊,如果你这么急切的话,你就为它下定义。”珠彭强烈要求道。“不运用特性去解释的话,要如何勾通任何涵意呢?你认为你将会出奇不意地领悟究竟实相吗?你需要使用文字与概念。你这个白痴!”他的朋友回复道。珠彭反击说:“如果你认为你能使用文字和概念来展现空性的话,那么你才是举世无双的蠢蛋!”他们继续这样彼此斗嘴、嘲笑对方。接着珠彭转而对我说:“你看,要是没有噶美堪布注解的版本,我要如何抵挡像这样的家伙?”后来,当帝亚·珠彭离开西藏,抵达锡金时,他告诉我:“我无法将那些书带在身边。我想要带着他们,我也确实尝试过,却没有成功。”“你怎么能把它们弄丢呢?”我悲叹道。“我对三宝发誓!你不在那里,没有看到失序与混乱的情况。没有人知道第二天早上是否还能活着,或成为一具死尸;像飘过秋日天空的云朵一样,没有任何事可以预料得到。那是个极度动荡与危险的时期。”“那是我们所置身的状况,你们却轻松地在锡金享受着美好时光。”至今,我仍时常想起那些注释,也就是康楚对噶美堪布提问所做的答复,原本会是对《知识宝藏》多么绝妙的画龙点睛之作!在楚布寺时,我幸运地见到了《百妙行大画卷》(TheGreatScrolllDepictingtheHundredWondrousDeeds);我将它视为这个世界上有意义的艺术作品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例证之一。在这件一幅接一幅的巨大画卷中,描绘了第五世噶玛巴在中国皇帝的宫廷里,所展现的一百种神迹;它的内容文字则是以中文、蒙古文、藏文,以及一种我不认识的文字,共四种语言所写成。这部惊人的画卷比四十只张开的手臂还要长,有好几尺高;上面画着六十位阿罗汉,他们是现身于低垂浓密云团上的圣者;再加上灌顶期间,发生于皇帝私人起居室里,包括皇帝如何见到本尊的坛城,以及那天升起了三个太阳等所有神奇事迹。我一直都不知道这幅画卷的存在,直到宗萨·钦哲来到楚布寺,并要求看它时,我才晓得。当我们摊开画卷的时候,宗萨·钦哲评论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从未见过任何像这样的东西!当其他大师在中国皇帝那里时,也展现了神迹,却也没有像这样。”有一天早上,宗萨·钦哲和我浏览了整幅画卷,并且从头到尾细读了所有解说。我听说这副画卷被做成了三幅复本:一幅在中国皇帝宫廷、一幅在楚布寺,另一幅则在许多世纪以前就毁于祝融。图画上有十九个由皇帝亲自盖下的认证印玺。这幅画卷如果能以书本的形式保存,肯定会很棒。我也试图取笑帝亚·珠彭没有将这幅珍贵的画卷带出来。不过,他再度反驳道:“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不是个强悍的人?你认为当我们出生入死时,你却闲散地坐在锡金,这就强悍了吗?”我对那番话能说什么呢?不过,我接着又记起了某件事,再次逗弄了他一下,我说:“那么是谁打包噶玛巴的行囊呢?我听说有一百名脚夫,却只扛着糌粑粉、干酪与干肉片。难道你就不能把一袋食物换成画卷吗?难道你不知道不丹国王已经表示愿意当功德主了吗?有谁会在国王担任赞助人时饿死呢?既然我说到了这件事,其他所有被抛在后头的身、语、意信物又该怎么说呢?”所有的玩笑搁在一旁,我真的很担忧这件珍贵的宝物已经遗失了。不过,后来我发现它安然无恙地存放在锡金。1、康卓·策琳·雀准(KhandroTseringChodron)目前住在锡金。她是索甲仁波切(SogyalRinpoche)的姑辈。2、莲花生大士的莲花冠被视为是一件“见即解脱”的圣物。3、这种精熟于觉知展现的灌顶,是一种最为博大精深的传承;它让弟子与无二了知的本性面对面,而在这之后的修持,则是为了要了悟念头与烦恼即是这种觉知的展现。4、“秘密封记”经常会限制伏藏法的传布,只能传给即将成为那个特定传承持有人的大师,或传给立誓要全心全意修持的人。5、为了要解释这个灌顶,容我引述莲花生大士的话:“觉知展现(awareness-display)的灌顶是由自性俱生圆满的佛所教授的,是自无上法身佛土(Akanishtha)法界的慈悲化现,他们为了立即唤醒具有最上福报的人而给予这个教授。因此,没有受过觉知展现的灌顶,是无法获致佛果的。所有过去的佛,都在领受了觉知展现的灌顶后觉醒了;每个当前成佛的人,也是领受了觉知展现的灌顶后才觉醒的;而每个在未来世成道的佛,也一样将在领受了觉知展现的灌顶后觉醒的。除非你已得到这个灌顶,否则是不可能成佛的。”6、完整的书名是《一盏驱除黑暗的灯:过去证悟者传统中直指心性的指引》(ALamptoDispelDarkness:AninstructionthatpointsdirectlytothenatureofmindinthetraditionoftheoldRealizedOnes;CrystalCave,RangjrngYeshePublication,1990)7、秋吉·林巴发掘并解码了几部密续,有些是包含在称为《七支深密轮》的伏藏法中,而他也带来了一部与《密藏密续》一样深奥的密续。仪轨的数量当然很多,然而能写下这种类型密续的伏藏师却极为罕见。尽管如此,我们祖古连着《八佛母》系统一起做到了!(祖古·乌金仁波切说明)8、那三尊是由酿惹、咕如·确旺与秋吉·林巴所发掘出的。(祖古·乌金仁波切说明)9、《八大成就法》的另一个版本的确存在于《大圆满三部》中,而《三部》中的口决部也包含了身为本空护法的九个空行母的法教系统。在体性上,这些空行母与化现为大圆满法教守护者的八位佛母是无别的。以这样来看,你可以说这些法教的精髓仍旧完好无损。男性层面的精髓呈现在多部仪轨的形式中,不过由于该文本遗失了,女性层面的精髓现在只在阿底瑜伽的护法形式中才找得到。最近,乌金·多杰(OrgyenTobgyal)从西藏带回这部文本,因此,现在它是《新伏藏》法的一部分了。这份刻印版本有二十页,我不确定他是否设法成功地接到了它的传承。
更新于:2023-09-22 13:3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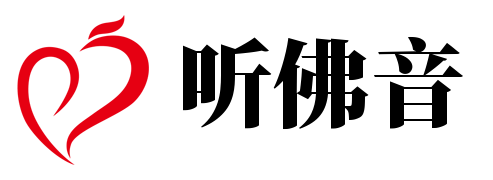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