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强法师:原始佛教之中道 第四章 无我中道
第四章 无我中道
就我之有无来说,有我见与无我见。世人及外道通常以有我为正见,以无我为非如实见。佛教反之,以无我为正见,以有我为邪见。我见与无我见从字面上看,分别是有见、无见所摄,但内外道所说之我见又与常断二见相关联,所以本文将探讨我之有无单独列出作为一章,以发掘佛教无我的真义。
为破除世人关于我之有见与常见,佛陀宣说无我,否认有常恒、独立、自在的主宰体。为破除世人关于我之断见,佛陀也说无常之我、变异之我、假名之我,以此成立业果相续与生死轮回。佛陀说无常恒我又不执无见、不堕断见,说假名我又不执有见、不堕常见,这远离有无二见、常断二边的无我见,即是原始佛教之无我中道。
一、世人我见
我,梵语为ātman,巴利语为attan,原意指气息,后引申为生命、自我、本质等。佛教经典中的我,通常是指五蕴身心中独立的主宰体,如《成唯识论》说“我谓主宰”。[138]我见,即认为有一真实我存在之见,如认为五蕴等是我。我所见,于五蕴等认为是我所有之见。我见、我所见都是基于我们的五蕴身心及其活动而产生的,如《杂·八○经》中佛说我、我所“从若见、若闻、若嗅、若尝、若触、若识而生”,[139]《杂·三○六经》说的更详细:
眼、色缘生眼识,三事和合触,触俱生受、想、思。此四无色阴、眼、色,此等法名为人。于斯等法,作人想、众生、那罗、摩[少/兔]阇、摩那婆、士夫、福伽罗、耆婆、禅头。又如是说:我眼见色,我耳闻声,我鼻嗅香,我舌尝味,我身觉触,我意识法。彼施设又如是言说:是尊者如是名,如是生,如是姓,如是食,如是受苦乐,如是长寿,如是久住,如是寿分齐。[140]
经中说的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根、尘、识三者和合而产生种种身心活动,我们将此个体身心活动的主体称为某人、某众生等。其它如“那罗、摩[少/兔]阇、摩那婆、士夫、福伽罗、耆婆、禅头”等都是人、众生、有情的异名。若是于有情自体,此身心活动的主体则称为“我”。基于种种分别,此主体“我”有此出生、有此姓名、有此衣食、有此苦乐、有此寿命,由此更为增长分别我执。外道也是基于生活经验而肯定有我,如《阿毗昙毗婆沙论》:
彼诸外道以何事故见我?
答曰:“愚于来去威仪法故,彼作是说:‘若无我者,谁来谁去,谁住谁坐,谁屈谁申耶?以有我故,能来去、住坐、屈申。复次,若无我者,则无见、闻、嗅香、知味、觉触、忆念,以有此事,必知有我。’”[141]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一个身心健全、智力正常的人,都有明确的自我意识。虽然刚出生的婴儿懵懵懂懂,浑然不知自他的种种社会分别,但在自身感受苦乐、饥饱时,也有哭笑的自我表达。儿童在眼看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觉触、意生法等身心活动中,在行往归来、饮食起居、屈伸低仰、语默动静等日常行为中,随着心智的成熟与知觉的经验积累,一方面确认自己身心的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确认自己的相对主观能动性,以及在这两者基础上的相对自由性,由此慢慢形成自我意识。到了青少年时期,这自我意识更为强烈,通常会有自我独立、自我张扬、自我实现的愿望。但如果这种愿望长期得不到满足或遇到重大打击,青少年可能会因此形成自卑、自闭、叛逆乃至反社会的人格障碍。相反,一个人如果自我意识模糊乃至丧失,除了醉酒、睡眠、昏迷等,那就是智障或癫狂了。所以在通常情况下,我们把一个人有没有明确的自我意识作为判断他是否心理健康、智力正常的一个重要指标。
这种自我意识,在佛典里称为我见,即认为在我们的身心当中,有一个独立的、有自由意志的“我”存在,这个“我”能主宰自己的身心及其活动。所以“我”有独立、主宰与自在义。
(一)我见、身见之类别
对于印度当时世间的种种我见,佛典做了一些归纳。如《杂·一六六经》中佛说:
何所有故,何所起,何所系著,何所见我,令诸众生作如是见、如是说:色是我,余则虚名;无色是我,余则虚名;色、非色是我,余则虚名;非色、非无色是我,余则虚名;我有边,余则虚名;我无边,余则虚名;我有边、无边,余则虚名;我非有边、非无边,余则虚名;一想、种种想、多想、无量想,我一向乐、一向苦,若苦、乐、不苦不乐,余则虚名。[142]
经中说外道中有人认为色是我,其余说法都不对,无色是我、色非色是我、非色非无色是我、我有边、我无边、我有边无边、我非有边非无边、我一想、我种种想、我多想、我无量想、我一向乐、我一向苦、我有苦有乐、我不苦不乐同样如此。这十六种我见中有些对于世俗常人来说可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这主要是印度外道根据自己所修学的冥想或禅定境界而说的。但此种种我见都不离五蕴,正如《杂·四五经》中佛说:“若诸沙门、婆罗门见有我者,一切皆于此五受阴见我。”[143]
基于我见,我们会认为一些东西是附属于我的或为我所拥有的,这称为我所见。比如,认为身体、精神、寿命等为我所有,或外在的名誉、地位、权势、财物及亲属等为我所有,这是我所见。我见、我所见都属于身见,或称有身见、自身见。身见,音译作萨迦耶见,即于五蕴集合之身起是我或我所有之见。如《法乐比丘尼经》中说:
彼见色是神,见神有色,见神中有色,见色中有神也;见觉……想……行……识是神,见神有识,见神中有识,见识中有神也,是谓自身见也。[144]
经中的“神”是“我”的另译,“觉”是“受”的另译。世人身见之类别,舍利弗在《增?利养品?第四经》中就色法来说有五种,即“色为我,色是我所,我是色所,色中有我,我中有色”。合五蕴,则共二十五种身见。[145]
我见、我所见是基于有身见而产生的,世间其它种种见也因有身见而起。如尊者梨犀达多在经中说“凡世间所见,或言有我……一切皆以身见为本”。[146]世间诸所有见,如南传《梵网经》中六十二见等,也皆以身见为本,正如《相应部》中说:“有己身见者,则存此等之诸见;无己身见者,此等诸见则不存在。”[147]
(二)我之常见与断见
我见是有见的一种,如果执我为常,则生常见。如《杂·一五二经》中说外道见:“有我、有此世、有他世,常、恒、不变易法,如尔安住。”[148]南传《梵网经》中讲到前际论者由四种根据说我是常,也由四种根据说我一分是常。无论是全部还是一分为常,这我都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在前世、今世、来世的时间迁流中,此“我”从此世转到彼世。汉传论典也通常把后际论者的十六种有想论、八种无想论、八种非有想非无想论等列入常见,因为都是基于有我而立论。印度婆罗门教到了《奥义书》时代,认为“梵”、“我”同质同源,如《杂·一五三经》中说外道见:“如是我彼,一切不二、不异、不灭。”[149]
断见者则认为此我在将来会归于断灭而无所有。汉传《梵动经》中讲到七种断灭论,如说由现生归断灭,或说由欲界归断灭,或说由色界归断灭,或说由无色空处归断灭,或说由无色识处归断灭,或说由无色不用处归断灭,或说由无色有想无想处归断灭。对于没有三界观念的一般世人,多持现生断灭论。
二、佛说无我
如前文所说,世人及外道有种种我见、身见,以有我为正见,或执我为常,或以为我将断灭。针对执我为常者,佛陀则以其无漏慧如实观照众生的痴迷与妄动根源于我执,不得解脱。佛陀正是明见我见的过患,立无我为正见,以离执去贪、成就解脱。要想把握佛陀无我的真义,必须首先了解我见的过患。
(一)我见的过患
由我见能随生我慢。如《杂·五八经》中佛说愚痴无闻凡夫于五蕴“见我、异我、相在”,而“于此生我慢”。[150]我慢是自我高举,自己不如人而觉得与人等,自己与人等而觉得高人一等。如果再觉得我是常,则我慢会坚固如高山。大梵天即是如此,自认为是自成、唯一、自在、为世界主的,如《阿[少/兔]夷经》:
我今是大梵王,忽然而有,无作我者。我能尽达诸义所趣,于千世界最得自在,能作能化,微妙第一,为人父母。我先至此,独一无侣,由我力故,有此众生,我作此众生。[151]
大梵天自认为“无作我者”、“为人父母”、“独一无侣”、“最得自在”,这是由我慢产生了尊佑论。众生因为有我慢故,导致五阴生漏而轮回相续,如《杂·一〇五经》中佛说“慢不断故,舍此阴已,与阴相续生”。[152]
另一方面,由我见又能生贪爱,如《杂·六二经》中佛说愚痴无闻凡夫无慧无明,“于五受阴说我系著,使心结缚而生贪欲”。[153]关于我爱,《杂·九八四经》中说从内外各生十八爱行,时间上又有过去、现在、将来之别,如是总说有百八爱行。这些爱行“为网”、“为胶”、“为盖”、“为覆”、“为众生障”,使众生“从此世至他世,从他世至此世”这样“往来流转”。[154]我见为无明之分,为前际生死根本;贪爱成就将来相续业果,为后际生死根本。众生就因为于五蕴见有我生爱,于是“无明所盖,爱系其首,长道驱驰,生死轮回,生死流转”,[155]出离轮回则遥遥无期。
因为由我见产生我执,由我执产生我慢、我爱、我贪,由此随生种种恶不善法,导致生死业果相续,陷入轮回不得解脱。所以《杂·五七经》中佛说“见我者即是行”,而缘行有识,缘识有名色,乃至纯大苦聚集。[156]
(二)佛说无我
世人根据日常身心活动的经验,认为个体身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能动性及自由性,于是执此身心活动的行为主体为我。基于我执,又希望或痴迷此我常恒不变,那这个常恒、独立、自在的主宰我到底存不存在呢?
1.破斥有我
佛陀并没有认为在这有情的五蕴身心当中存在一个常恒、独立、自在的主宰“我”。佛陀要破斥我见,就首先要破斥此我之主宰性。
外道通常以有我为正见、无我为邪见,如萨遮尼犍子就是代表。他听说佛陀以无我见教授弟子,于是决定与佛陀公开辩论。萨遮尼犍子比喻说,如世间万物都是依于大地而出生、成长、圆满一样,人间的种种善恶都是依于色、受、想、行、识等五蕴而出现、增长、成就,所以此五蕴等即是我。佛陀也以比喻反问,如一国之王能自在地处罚有罪者、奖赏有功者,那作为主宰的“我”能随意自在地要五蕴这样、不得那样吗?佛陀如是再三反问,萨遮尼犍子先保持沉默,最后才硬着头皮回答不能。佛陀接着说明以五蕴无常、苦而说五蕴无我,萨遮尼犍子惭愧失色。[157]
又因为五蕴身心有苦、不得自在故,佛说五蕴无我。如《佛说五蕴皆空经》:
色不是我。若是我者,色不应病,及受苦恼,我欲如是色,我不欲如是色。既不如是,随情所欲,是故当知,色不是我。受、想、行、识亦复如是。[158]
如果五蕴如色等是我,即能随意主宰的话,则色不应病坏而有种种苦恼,我要这样的色即能要这样的色,我不要那样的色即能不要那样的色。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我们所愿地想要怎样就能怎样,所以说五蕴如色等不是我。
内六处同样有苦、不得自在,如《杂·三一八经》中佛说:
眼非我。若眼是我者,不应受逼迫苦,应得于眼欲令如是、不令如是。以眼非我故,受逼迫苦,不得于眼欲令如是、不令如是。耳、鼻、舌、身、意亦如是说。[159]
如果内六处如眼等是我,则眼等不应受种种苦恼所逼迫,我要令眼等这样即能这样,我不要令眼等那样即能不要那样。而实际情况是,眼等时常受种种苦恼所逼迫,也不得令眼等这样那样,所以眼等内六处不是我。
有情之五蕴及根身活动又是因缘所生、无常变化的,如《杂·二七三经》中佛说:
譬如两手和合相对作声,如是缘眼、色生眼识,三事和合触,触俱生受、想、思,此等诸法非我、非常,是无常之我,非恒、非安隐,变易之我。[160]
因为有情的五蕴及其身心活动等是因缘所生的,正如一个巴掌拍不响,所以此非独立之“我”,又是“非恒、非安隐”的,故是“无常之我”、“变易之我”。因为没有常恒性与独立性,所以此五蕴也就不能称之为“我”,即如此经中说“此等诸法非我”。又如前面佛陀所分析,我们其实并不能随意主宰五蕴身心,相反为五取蕴所生的苦恼所逼,不得自在。正如《增?邪聚品?第十经》中佛说:“此无常义即是苦,苦者即无我,无我者即是空也。”[161]所以在我们的五蕴身心中,根本不存在一个常恒、独立、自在的主宰“我”。
2.一切法无我
从《阿含经》中来看,佛陀主要是基于有情生命现象——蕴、处、界的无常、苦而说无我或非我的,如《杂·八四经》中佛说“无常则苦,苦则非我”[162]。佛陀对有情世间这种无常、苦、无我有极为深刻地体认,以致把它们称为佛法之本而确定为佛法的特质。如《增?增上品?第四经》中佛说:
诸比丘,欲得免死者,当思惟四法本。云何为四?一切行无常,是谓初法本,当念修行;一切行苦,是谓第二法本,当共思惟;一切法无我,此第三法本,当共思惟;灭尽为涅槃,是谓第四法本,当共思惟。[163]
关于此经四法本中的“一切法无我”,在同样讲到四法本的《增?四意断品?第八经、第九经》均作“一切诸行无我”,[164]《增?八难品?第三经》作“一切行无我”。[165]没有提到四法本的其它诸经或说“诸法无我” [166]、 “一切法无我”[167]、“一切无我”[168]、 “一切非我”[169],虽然文字表述有些差别,含义却一样。
佛说“一切无我”、“一切非我”,那什么是“一切”?《杂·三一九经》中佛说:
一切者,谓十二入处,眼色、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法,是名一切。若复说言此非一切,沙门瞿昙所说一切我今舍,别立余一切者,彼但有言说,问已不知,增其疑惑。所以者何?非其境界故。[170]
十二入处即内六根与外六尘,此六根六尘相接而生六识,根、尘、识和合而生触,由触生诸受等。经中说“一切者,谓十二入处”,即是说此有情五蕴身心及其活动名为“一切”。有情所能见闻觉知的即此一切,所能贪著执取的即此一切,业果所能相续、生死所能轮回的也即此一切,生厌离欲、出世解脱的也即此一切,所以对于有情,除此以外,别无一切。外道于此不知不见、不了不达,所以“非其境界”。
佛说“一切法无我”,那什么是“一切法”?《杂·三二一经》中佛说:
眼及色、眼识、眼触,眼触因缘生受:若苦、若乐、不苦不乐,耳……鼻……舌……身……意、法、意识、意触,意触因缘生受:若苦、若乐、不苦不乐,是名为一切法。若复有言此非一切法,沙门瞿昙所说一切法我今舍,更立一切法者,此但有言,数问已不知,增其痴惑。所以者何?非其境界故。[171]
如“一切”所说,有情的六根六尘相接而生六识,根、尘、识和合而生触,由触生诸受,此等五蕴身心及其活动又名为“一切法”。同样,有情所能见闻觉知的即此等法,所能贪著执取的即此等法,业果所能相续、生死所能轮回的也即此等法,生厌离欲、出世解脱的也即此等法,所以对于有情,除此以外,别无一切法。外道于此不知不见、不了不达,所以“非其境界”。
就原始佛教来说,佛陀以人为本,直指解脱。而与生死解脱无关的外界种种存在及世间玄谈的形而上学,佛陀则不关心,如十四无记等。所以佛陀基于有情五蕴身心及其活动而施设“一切”、“一切法”、“一切有”[172]。而此等“一切”、“一切法”、“一切有”是因缘所生的、无常变化的,所以也即是“一切行”。
(三)佛说无我的利益
世人种种我见都不离五蕴,正如《杂·四五经》中佛说:“若诸沙门、婆罗门见有我者,一切皆于此五受阴见我。”[173]为什么会于五受阴见我呢?南传《相应部》中佛比喻说如人取来明镜才从中看见自己一样,若于五蕴有执取,则会执以为我;如人不取明镜则不会从中看见自己一样,若于五蕴无所执取,则不会执以为我。所以经中说“计取故有我,不取者则不计”。[174]正是因为世人与外道等执以有我,因此不得尽苦、不得究竟解脱。如经中佛说:
若诸沙门、婆罗门于世间所念谛正之色,作常想、恒想、安隐想、无病想、我想、我所想而见,则于此色爱增长。爱增长已,亿波提[175]增长。亿波提增长已,苦增长。苦增长已,则不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我说彼不解脱苦。
譬如路侧清凉池水,香味具足,有人以毒着中。阳春之月,诸行路者风热渴逼,竞来欲饮。有人语言:“士夫,此是清凉色,香味具足,然中有毒,汝等勿饮。若当饮者,或令汝死,或近死苦。”而彼渴者不信而饮,虽得美味,须臾或死,或近死苦。[176]
若是于色起常想、恒想、安隐想、无病想,即是于色起我想、我所想,随即于我、我所起贪爱,因此纯大苦聚集,如饮毒水。如《杂·一一〇经》所说,佛陀为了弟子“得离疑惑”、“令得安隐、令得无畏、调伏寂静、究竟涅槃”故而宣说无我教法。[177]所离的疑惑,即是于真实无我的疑惑。由信解无我故,于五蕴生厌、离欲,而成就智慧、解脱、解脱知见等“三无上”。佛说无我,最终是为了弟子涅槃解脱。
《杂·三○六经》中佛说若于五蕴身心活动中只见无常、有为诸法而不起我见、我所见,则为见法。[178]如进一步观察无我,可断五下分结,如《杂·六四经》中世尊所说偈:
法无有吾我[179],亦复无我所,我既非当有,我所何由生?比丘解脱此,则断下分结。[180]
又通过无我观能远离我慢得解脱,如《弥醯经》中佛说“若比丘得无我想者,便于现法断一切我慢”,乃至得“灭尽”、“涅槃”。[181]所以佛在《大本经》中说“若学决定法,知诸法无我,此为法中上,智慧转*轮”。[182]佛陀本人虽然极尽方便广为说法、利益人天,但由于“心无所著”,而说“何处有我为彼比丘说法”。[183]又因为“一切行无常,生者必有死”,[184]连三世诸佛也不可避免,所以佛在《增?听法品?第五经》中说“若欲礼佛者,过去及当来,现在及诸佛,当计于无我”。[185]我们常说诸供养中法供养为最,所谓法供养,正如于蕴处界如实观察无我。
佛陀基于对有情无常、苦、生死轮回等生命现象深入、透彻地体察,而确认有情世间没有任何独立的永恒的主宰体——我。无我说为佛陀区别外道的不共见,而使得佛陀的教说卓而不群、超凡入胜。佛陀最初度化五比丘时,先说《转*轮经》[186],憍陈如率先见法,佛陀而后说《无我相经》[187],五比丘才先后证得阿罗汉。
三、佛说假名我
“我”的梵语为ātman,在印度婆罗门教的《吠陀》经典中,原指生命个体的气息,慢慢演变成个体生命现象中有主宰性、不变性、独立性的本体“我”,所以“我”在印度传统宗教哲学中是指永恒、独立、有主宰性的真实本体。无我,梵语 anātman,则是在“我”之原语前加一否定之前缀“an”,汉传经典中也翻译为“非我”,即是说此并非真正之“我”。佛陀在经典中首先也承认有情生命现象的存在,如经中所说的十二因缘、四圣谛、八正道等,都是基于有情身心活动而宣说的有情轮回之原因与脱离轮回之方法。但佛陀为了有情于五蕴身心生厌、离欲、解脱,而说这无常、苦的有情五蕴身心并非是那个我们所认为的永恒、独立、有主宰性的“我”,正如《杂阿含经》中佛说“无常即苦,苦即非我,非我者亦非我所”[188],或者“无常者则是苦,苦者则非我,非我者则非我所”[189]。
(一)对佛说无我的疑惑与误解
无我为佛教的不共正见,以此标显佛法的特质。而无我表面上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大有出入,所以世人及外道难以理解与接受。如众多外道因为佛陀说无我而认为是断灭论者,说“沙门瞿昙作断灭、破坏有教授”。[190]又如佛陀成佛后初到摩揭陀国为国王及其臣民说无我时,摩揭陀人心想,若五蕴无常、无我,那“谁活、谁受苦乐”?[191]即使是佛陀弟子,由于自我意识根深蒂固,也对无我说有疑惑。如一比丘“起恶邪见而作是念”:“若无我者,作无我业,于未来世,谁当受报?”[192]同样是疑惑行为与果报的主体。他们的疑惑在于没有我了,那有情身心活动的行为与果报的主体是谁?如果没有任何行为主体,那对于社会犯罪行为该追究谁的法律责任?若无人可追究,那整个社会不就乱套了吗?
另外于我贪著重者,则于无我说感到恐怖。如《杂·六四经》中佛说愚痴凡夫、无闻众生怖畏于“无我、无我所”,[193]《阿梨咤经》中则说到一些人听闻无我教法后便“内有恐怖”:“忧戚烦劳,啼哭椎胸,而发狂痴”。[194]
又如阐陀,虽然也闻思过“一切行无常,一切法无我”,但是因为有贪欲而取著于“我”,而于“爱尽、离欲、灭尽、涅槃”生起恐惧。[195]这是于无我、解脱生起恐惧。世人我慢、我爱、我贪是依我见而生的,佛陀为断世人我慢、我爱、我贪而说没有独立、常恒的主宰“我”。但因为很多人于佛法之缘起中道、出离解脱不知不见、不了不达,直认为佛说无我为断灭,由此起疑惑、生恐怖。
佛陀另一方面也说业报与轮回,说世人有神识入胎从此生到彼生,但有[口*荼]帝比丘鸡和哆子生如是恶见:“我知世尊如是说法:今此识往生不更异。”理由就是“此识说、觉、作、教作、起、等起,谓彼彼作善恶业而受报也”。[196]这是以识为轮回的主体而生起常见。
(二)假名我的安立
以上对佛陀无我教法的疑惑与误解,都来自于何为善恶行、业果相续与轮回的主体。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主体,那业果相续与轮回则有如高楼无基、无从安立。如此种种疑惑,都是因为于佛说的无我中道没有理解到位而起的。如前文“佛说无我”中,佛陀所破斥的“我”,是指独立、常恒的主宰体,但佛教也安立缘起有的无常变化的“假名我”。如《阿毗昙毗婆沙论》中说:
我有二种:一假名我,二计人我。若计假名我,则非邪见。若计人我,此则邪见。[197]
论中所说的“假名我”,即世俗中因缘而有的无常之我。由此假名我,得以确立世俗社会中个人与国家、集体、家庭、亲朋好友等各种社会关系中的责任与权力,这样才能形成社会的有序、和谐、稳定。否则,如外道恶取空者认为无我、无众生、无善恶业、无善恶业报,那整个社会还不陷入无政府状态?
佛陀关于“我”非无见论者,也非断灭论者,不认为有情凡夫死后断灭无所有,相反,佛陀说在轮回中有业果相续不断。有情之六根生时非从前世来,终时非往来世去,此五阴消失了而有另外的五阴相续,有情在三世轮回中并没有一个常恒不变的我。所以在这三世的业果相续中,《第一义空法经》[198]中说“有业报而无作者,此阴灭已,异阴相续”。此“作者”即独立、常恒的主宰体“我”是不存在的,所以此经名为《第一义空法经》。所谓“异阴相续”,即经中说的“俗数法”,为缘起有的无常变化的相续五阴,世人假名为“我”。即没有常恒的“主宰我”,但有无常变化的“假名我”。此“假名我”,佛在《阿含经》中则说为“无常之我”、“变异之我”,如《杂·二七三经》:
譬如两手和合相对作声,如是缘眼、色生眼识,三事和合触,触俱生受、想、思,此等诸法非我、非常,是无常之我,非恒、非安隐,变易之我。[199]
因为有情的五蕴身心活动等是因缘所生的,故是“无常之我”,是“非恒非安隐”的“变易之我”,非永恒、独立、有主宰性的“我”,所以经中说“此等诸法非我”,正如《杂·一九六经》说“一切非我”[200]。
从原始佛教来看,佛陀主要是基于有情生命现象的无常、苦而说“无我”或“非我”的,但也没有否认作为轮回与业果主体的“假名我”、“无常之我”、“变异之我”,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有时经典中也说到“有我”。如《杂阿含经》中佛说阿罗汉“正复说有我,我所亦无咎”,这是因为诸阿罗汉:
已离于我慢,无复我慢心,超越我我所,我说为漏尽。于彼我我所,心已永不著,善解世名字,平等假名说。[201]
此“我”之假名说,经典中有以车、屋等比喻说明,如《阿含经》:
(尸罗比丘尼说偈言:)
汝谓有众生,此则恶魔见。唯有空阴聚,无是众生者。
如和合众材,世名之为车。诸阴因缘合,假名为众生。[202]
(尊者舍梨子告诸比丘:)诸贤,犹如因材木、因泥土、因水草覆裹于空,便生屋名。诸贤,当知此身亦复如是,因筋骨、因皮肤、因肉血缠裹于空,便生身名。[203]
车与屋是由众多材料组合而成,在此之前并没有一个车与屋存在,此车与屋是因缘而有的。有情的身心同样是由诸蕴因缘和合而无常有的,在此之前并没有一个这样的有情身心存在,所以假名为“众生”、“我”。
基于此无常之“假名我”,佛陀本人在日常生活中与经典中也说“我”,如说“我昔于色味有求有行”[204]、 “我不与世间诤,世间与我诤”[205]、“尔时大典尊……即我身是也”[206]。这无常之“假名我”作为业果相续的主体[207],佛陀也称之为“我”、“己”、“自”,如“比丘自知我有尔所信、戒、闻、施、慧、辩、阿含及所得,是谓比丘为知己也”[208]、 “当自炽燃……当自归依”[209]、 “于现法中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210]。
《杂·三○六经》中就此“假名我”,无论说为人、众生还是士夫等,佛说此等“为想”、“为志”、“为言说”,“皆悉无常、有为、思愿缘生”,“彼则是苦”。若是于此无常、苦之假名能“爱尽”、“无欲”、“灭尽”而“无有我”,则能证入“涅槃”。经中佛说“如是知、如是见,则为见法”。[211]
四、无我中道
针对世人与外道中执我为常恒者,佛陀否认有常恒、独立、自在的主宰体,而说无我或非我。但佛陀也决非为无见论者或断见论者,也依缘起法说假名我,作为轮回与业果相续的承载体。佛陀说无我,是远离有无二见的。轮回中虽然有异阴相续,却是无常变异的,而生死轮回之流本身又并非不可截断、超脱。佛陀说无我,又是远离常断两边的,如《杂?一〇五经》:
仙尼当知,有三种师。何等为三?有一师,见现在世真实是我,如所知说,而无能知命终后事,是名第一师出于世间。复次,仙尼,有一师,见现在世真实是我,命终之后亦见是我,如所知说。复次,先尼,有一师,不见现在世真实是我,亦复不见命终之后真实是我。仙尼,其第一师见现在世真实是我,如所知说者,名曰断见。彼第二师见今世后世真实是我,如所知说者,则是常见。彼第三师不见现在世真实是我,命终之后亦不见我,是则如来、应、等正觉说,现法爱断、离欲、灭尽、涅槃。[212]
第一师见现世真实有我而不知有后世,这是断见;第二师见今世后世真实有我,这是常见;第三师见世俗人有今世后世而离断见,但无真实之我而离常见。第三种见即是如来无我之中道正见,是远离常断两边的,如南传《经集》中说圣者“彼乃无我无常见,断见非我亦不得”。[213]
佛陀否认有常恒、独立、自在的主宰我,同时在三世业果相续中说有假名我,所以我们也就自然理解佛对于外道三问有没有我而不答了,如《别译杂?一九五经》中佛告阿难:
于先昔彼问一切诸法,若有我者,吾可答彼犊子所问。吾于昔时宁可不于一切经说无我耶?以无我故,答彼所问则违道理。所以者何?一切诸法皆无我故,云何以我而答于彼?若然者,将更增彼昔来愚惑。复次,阿难,若说有我,即堕常见;若说无我,即堕断见。如来说法,舍离二边,会于中道,以此诸法坏故不常、续故不断,不常不断。[214]
佛陀给阿难解释说,如果有我,则佛可回答外道的问题。但佛长久以来说无我,那佛如何以我来回答问题?又如果执于有我,则堕常见;如果执于无我,则堕断见。而如来说无我是依缘起中道而说的,即“坏故不常、续故不断”而“不常不断”。
虽然经中说是“不常不断”之无我中道,但其内容还是讨论“我”之有无。如《俱舍论》中以牝虎衔子对“我”之有无做了十分恰当的比喻:
观为见所伤,及坏诸善业,故佛说正法,如牝虎衔子,
执真我为有,则为见牙伤;拨俗我为无,便坏善业子。[215]
牝虎衔子,用力过重则牙伤虎子,用力过轻则虎子堕地。同样地,如执真常之我为有,则为常见所伤不得解脱;如执世俗假名、无常变化之我为无,则为断见所伤败坏善业。所以佛陀处中说法,不常不断,也即是不有不无。
无我中道从认知上,否定的是常恒、独立、有主宰性的我,但并没有否认有情五蕴身心活动等“无常之我”。也正是这“无常之我”,作为业报与轮回的主体,所以佛陀才会预记某某将来生善趣天上某某将来生三恶道。
另外在《中阿含经》中,佛陀将真实有我、真实无我列入六种邪见,如经:
彼作如是不正思惟,于六见中随其见生而生真有神[216],此见生而生真无神,此见生而生神见神,此见生而生神见非神,此见生而生非神见神,此见生而生此是神,能语、能知,能作、教作,起、教起,生彼彼处,受善恶报,定无所从来,定不有,定不当有,是谓见之弊,为见所动,见结所系。凡夫愚人以是之故,便受生、老、病、死苦也。[217]
六种邪见即此我真实有、此我真实无、此我生有我想、此我生无我想、此无我生我想、此即是我等,经中说这些是“见之弊”、“见结所系”,因此“受生、老、病、死苦”。关于我之有无见,《起世经》也有这样类似的说法:
诸比丘,思惟有我,是为邪思;思惟无我,亦是邪思。乃至思惟我是有常、我是无常,有色无色、有想无想、及非有想非无想等,并是邪思。诸比丘,此邪思惟是痈是疮,犹如毒箭。其中若有多闻圣达智慧之人,知是邪思如病、如疮、如痈、如箭,如是念已,系心正忆,不随心行,令心不动,多所利益。
诸比丘,若念有我则是邪念,则是有为,则是戏论;若念无我,亦是戏论,乃至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悉是戏论。诸比丘,所有戏论皆悉是病,如痈如疮,犹如毒箭。其中所有多闻圣达智慧之人,知此戏论诸过患已,乐无戏论,守心寂静,多所修行。[218]
经中说思惟有我、无我都是“邪思”,念有我、无我悉是“有为”、“戏论”。关于我之有无、常无常、有色无色、有想无想等外道见,在南传《梵网经》中也都有说到。佛陀说无我,是说没有独立、常恒的主宰我,但有缘起而有、无常变化的“假名我”作为业果相续的承载体。外道所说的无我,既没有常恒我,也没有无常我,是无有见。从实践意义上说,如果如外道一样恶取空,于无我执著而取断灭,则不得解脱,如《净不动道经》中佛告阿难:
若比丘如是行,无我、无我所,我当不有、我所当不有,若本有者便尽得舍。阿难,若比丘乐彼舍、著彼舍、住彼舍者,阿难,比丘行如是,必不得般涅槃。
……
若比丘如是行,无我、无我所,我当不有、我所当不有,若本有者便尽得舍。阿难,若比丘不乐彼舍、不著彼舍、不住彼舍者,阿难,比丘行如是,必得般涅槃。[219]
若是比丘于无我依于有无中道不取、不著、不住,则必得般涅槃。这些经文所说的无我中道,则是超越有无两种边见。
虽然无我是佛法的基调,但佛陀并没有忽视世俗假名我,通过广说蕴、处、界等分析有情的身心及其活动,让我们明白五蕴之缘起性、无常性、不自在性与无我性。外道在探究有情身心及轮回的问题时,或说命即是身,或说命异身异,而有此二边。对于身命二者的关系,佛陀依缘起确立中道见,如《杂?二九七经》:
彼见命即是身者,梵行者无有;或言命异身异者;梵行者亦无有。离此二边,正向中道,贤圣出世、如实、不颠倒正见所知,所谓缘无明行……[220]
所谓命即是身者,即认为身与命是一,其中常见者认为在生死轮回中此身、命常恒不变,断见者则认为有情死亡后身命俱灭。所谓命异身异,即身与命是二,各自独立,其中常见者认为在生死轮回中命会舍此身而就彼身,断见者则认为命与身先后坏灭。此中所说的命,与外道之灵魂、佛教之我大致相当。关于身与命的关系,佛陀依缘起而说不一不异的中道见,即舍离命即是身与命异身异的边见,不做无益的争论,而说无明缘行乃至老死,无明灭则行灭乃至老死灭,以此说明生死轮回的原因与究竟解脱的道理。虽然“身”“命”两者与“我”在概念上不同,但身与命同属世俗我的生命现象,所以本章“无我中道”中述及佛陀身与命不一不异的中道见。
为破除世人关于我之有见与常见,佛陀宣说无我,否认有常恒、独立、自在的主宰体。为破除世人关于我之断见,佛陀也说无常之我、变异之我、假名之我,以此成立业果相续与生死轮回。佛陀说无常恒我又不执无见、不堕断见,说假名我又不执有见、不堕常见,这远离有无二见、常断二边的无我见,即是原始佛教之无我中道。但因为众生长夜执持邪见、邪行,他们很难理解佛陀的无我教法,而误解佛陀为无有见者或断灭论者。如佛陀在《杂?四〇五经》中比喻说“一毛为百分,射一分甚难,观一一苦阴,非我难亦然”。[221]将一根毛发再分为百根更细的毫毛,用弓箭射中其中一根细毫毛,这是很难的。而观五阴是苦、非我,这比前者更为困难。所以只有超脱有无、常断的边见,才能真正深刻地体会离执去贪、直指解脱的无我中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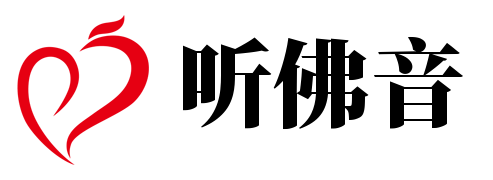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