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苦之道-尊者阿姜摩诃布瓦实修体验
本文转载自网络,作者不详。
阿姜 曼——契迪龙寺
( Wat Chedi Luang )这是清迈市区内最著名的寺庙,寺中有一座宏大的四方形佛塔,建于1411年,高近90米,宽45米。1545年清迈发生一次大地震,佛塔的尖顶一夜之间塌毁,现在所见是平顶的佛塔,仅余60米,且露出塔内的金身佛像。佛塔的四面雕有精致的龙头,龙身则随着阶梯而上;塔身也有大象支撑着,其中也因地震崩坏,但是一点也不见减损他的雄伟壮观。
契迪龙寺的大殿,背后是高大的佛塔
契迪龙寺规模很大,除了佛塔外,还有许多佛殿,其中有一座非常精美的佛殿,里面供奉的是泰国伟大的森林禅师——阿姜曼(Ajahn MunBhuridatta)的塑像,他是20世纪泰国十分有名的法师,弟子遍布在世界各地。
阿姜曼• 布里达陀 (1870-1949)阿姜曼1870年出生于泰国东北部乌东.拉贾泰尼省乡间的邦堪蓬村,于1893年出家为僧,从此一生游方于泰国、缅甸、寮国,大部分时间在林间梵行。他与老师阿姜索一起,振兴了泰国林居禅修传统,吸引了大批弟子,之后传遍整个泰国,以至海外几个国家。
阿姜摩诃布瓦(Achaan MahaBoowa1913~)在泰国东北部的森林苦行僧传统里,是一位著名的住持与老师。他读了几年的基本佛法后,精通巴利经典,之后开始禅修。阿姜摩诃布瓦于森林禅修数年,其间大多时间接受说寮国话的老师阿姜曼(译按:有摩诃布瓦著《尊者阿迦曼传》)的指导,这位老师是本世纪泰、寮森林最著名的老师之一,他出名的是对禅定与入观的教法、巨大的影响力及严厉的教学方式。据说阿姜摩诃布瓦去见阿姜曼之前,由于长时间的练习,已经精通了佛教的一些禅定方法,并于静坐中获得了极大的喜悦,仅仅是这样的精通,已经是很大的成就。然而,阿姜曼见到他时,却严厉地告诉他禅悦与智能的不同,然后送他离开,到森林里修习更多东西。经历此次斥责,阿姜摩诃布瓦有好几年的时间,再也无法进入高度喜悦的定境,但是,当他最后再度获得时,同时获得了大智能与内观力。
阿姜 查(AjahnChahPhothiyan),他也是泰国近代最著名的法师之一,9岁出家,20岁受比丘戒,1946年通过高级正规佛学课程考试后,开始托钵行脚,寻师访道。1948年他拜见了阿姜曼,获得重要的启发,改变了修行方法。追随者渐多,建立了巴蓬寺,目前在世界各地有200所分院。
用玻璃保护的阿姜曼法师塑像栩栩如生
阿姜 曼•布利达陀(1870-1949),Ajahn Mun Bhuridatta,20世纪最伟大的森林禅师,1870年生于泰国紧邻老挝与柬埔寨的乌汶省。从当时到现在,那里都是不毛之地,不过也正是这块土地的贫瘠与人民的和善性格,成就了世间稀有的心灵深度。
阿姜曼年轻时拥有活泼的心智,他在即兴歌谣等民俗艺术方面表现优异,并热衷于心灵修行。在成为比丘之后,前往追随当地一位杰出的森林比丘阿姜扫(AjahnSao),向他学习禅定,并了解到严持戒律对于心灵进步非常重要。他成为阿姜扫的弟子,积极投入修行。这两个元素(即禅定与严格的戒律),虽然从现在有利的角度来看可能并不起眼,然而,当时戒律在整个地区已变得非常松弛,而禅定更是受到很大的怀疑——可能对黑暗艺术有兴趣的人,才会笨到去接近它,它被认为会让人发疯或使心灵着魔。
阿姜曼适时且成功地对许多人解释与证明禅定的功效,并成为僧团更高行为标准的典范。此外,虽然地处偏远,他仍成为全国最受敬重的心灵导师。几乎所有二十世纪泰国最有成就与最受尊敬的禅师,若不是直接师承于他,就是受到他的深刻影响,阿姜查也是其中之一。
灭 苦 之 道——尊者阿姜 摩诃布瓦谈禅修经历(开示汇编)英译者 迪克•西拉勒塔诺比丘Anicata中译笔记,供参考本文非商业性
The Direct Route to the End of All SufferingFrom The Path to ArahantshipA Compilation of Venerable Ãcariya Mahã Boowa’s Dhamma TalksAbout His Own Path of PracticeTranslated from the Thai by Bhikkhu Dick Sïlaratano
佛教在当前, 只剩下了佛陀的言辞。只有世尊的教导, 也就是经文还保留着。 请注意这个现象。 由于“杂染”的污染性造成的腐败,当今佛教界, 人们已经不再按照真正的精神原理进行修持。我们身为佛教徒, 却允许心不停地焦躁、混淆, 被来自四面八方的杂染吞没。这些杂染紧紧控制了人心, 我们无论作多少努力,也难以克服它们的影响。绝大多数人, 甚至根本没有兴趣试着去克服。他们只是两眼一闭,被杂染的攻势压倒。他们甚至根本不作一点努力去抵制。因为缺乏“念住”, 看不见那些思想的后果, 他们一切的身、语、意,都是被杂染击败的结果。 很久以前他们就降服于那些毁灭性的力量, 到现在, 已经没有什么动力去制服妄念了。“念住”不在了,杂染为所欲为, 影响着人们的白天黑夜、一举一动。 就这样, 到处给人带来越来越大的负担与压力, 造成心智之苦。佛陀时代, 他的直系弟子依法修持, 是真正的行者。他们为了尽快超越苦, 舍离了世界。无论社会地位、年龄、性别怎样,一旦出家接受佛陀的教导, 他们就放下旧习, 在身、语、意上遵从佛法。从此以后, 那些弟子们把杂染扔到一边,不再受它的左右。他们全心全意、把精力放在清净心智、洗涤杂染的努力上。本质上, 正精进, 与行者保持稳定、持续的念住、不停地观察心念, 意思是相同的。“念住”监督着我们任何时刻、任何姿势的思维与情绪活动,这就叫做“正精进”。 无论是不是在作正式禅定, 如果我们精进努力, 使心定驻于当下,就能始终抵御杂染的侵袭。杂染是不懈不怠的, 它们不停地制造有关过去、将来的念头, 扰乱心智, 使它离开当下,离开支持我们修行的念住。因此, 行者不要让心游荡出去, 想那些关于过去、未来的俗念。这种念头总是带着杂染,会妨碍修行。行者必须专注于内心, 培养对内心世界的知觉, 而不是跟着杂染出去关心世俗事务。 这一点至关重要。许多行者不能得到满意的成果, 主要原因是, 在禅定基本原则的坚持方面, 决心不够。 我总是教弟子在修行中保持准确性,在禅定中要有特定目标。那样一定会有成果。找到一个合适的专注对象, 让心做好准备工作, 是很重要的。我通常建议用一个预备性的禅定词汇,通过在内心连续重复, 如一具铁锚, 很快使行者的心静止下来, 进入定境。 如果行者只是把注意力集中于心的知觉,而没有一个禅定用词那样把念钉住, 结果肯定是靠不住的。心的知觉太精细, 不能为“念住”提供坚实的基础, 用不了多久,心就响应杂染的召唤,去漫游、遐想、走神。修行变得不规则。有时候看上去进展顺利、几乎毫不费力,后来却突然意想不到地艰难起来。修行步子一不稳, 所有表面进展就不见了。修行的自信动摇了, 心开始挣扎。 不过,如果我们有一个禅定用词作为锚, 让“念住”稳固扎根,心就一定会尽快进入禅定的宁静与专注状态。并且也能轻松地保持在那个静止状态。我这里讲的, 是个人经验。我最初开始禅定时, 缺乏一个坚实的基础。 我还没有找到固守心念的正确方法, 修行时涨时落。进步一阵子,很快又退步, 回到原地, 等于没有学到什么。开始时我极其用功, 心进入了“奢摩他”。感觉象座山一样稳定扎实。那时候还缺乏适当的方法来保持这个状态, 我却感到自满、轻松起来。 就在那时, 修行退步了。它开始退步,我却不知怎样逆转。我因此苦苦思索, 要找一个让心稳定下来的坚实基础。 最后得出结论, 心跑掉了,是因为我的基础不牢。我缺乏一个禅定用词作为注意力的聚焦点。我被迫重新开始修。这次我打下一个坚固的桩, 不管发生什么, 坚定地抓住它。 这个桩就是“哺-哆”(buddho),意思是对佛陀的忆念。我就把禅定用词“哺-哆”当成唯一的专注目标。我在内心除了重复“哺-哆”,不去管其它。“哺-哆”是我的唯一目标,同时我也确保念住始终在把握和指导我的努力。那些关于进步、退步的想法全给放在一边。发生什么, 就让它发生。我下决心不再落入旧的思路:回顾过去修行怎样进步、怎样退失; 接着又幻想未来, 希望发一个大愿, 过去的自在感会再回来。一直这样想,却不去创造实现愿望的条件。我只是希望有进步, 不能实现时又感到失望。实际上, 成功的愿望并不会带来成功;只有带着“念住”的努力才会有成就。这一次我下决心, 无论发生什么, 就让它发生。为了进步、退步而烦恼, 是焦躁的源头,那样会分散对当下和当前工作的注意力。只有带着念住、重复“哺-哆”, 才能防止修行中的上下起伏。把心的知觉集中在即刻当下,至关重要。不要让心念分散开来, 干扰禅定。为了灭苦而精进禅修时, 你在正道上每走一步, 都得全力以赴, 不可有一点保留。为了体验最深的奢摩他, 获得最深的智慧,你不能半心半意、有气无力、缺乏修行的基本原则, 永远摇摆不定。修行不能够全心全意的投入, 行者一连修几世,也不会有正确的结果。在修行的初始阶段, 你必须找一个“明确的禅定对象”,把心定在上面。不要随便找一个象“心的内在知觉”这样的模糊对象。没有特定的专注对象来抓住心,几乎不可能防止注意力涣散。这样做会失败。到头来你会因为失望而放弃努力。“念住”一旦失去焦点, 杂染就会冲进来, 把你的思路扯到遥远的过去、渺茫的未来。 心变得不稳定, 在思维的风景区游荡,永远没有一刻的静止与满足。行者就是这样子退步, 眼睁睁看着修行失败。唯一的解药, 是有个单一而不复杂的专注中心;比如一个禅定用词、或者呼吸。你选择对自己最合适的, 把注意力持续放在那个目标上, 不要去管其它一切。全心全意至关重要。假定你选择呼吸作为集中目标, 就要让自己对每一次入息、每一次出息完全保持知觉。要注意气息的动态感,把注意力放在感受最明显、最敏锐的部位:例如鼻尖部位。你对气息何时进、何时出要有确切的知觉。但不要跟着呼吸走-只是专注于它进出的那一点。如果你觉得有帮助,可以把呼吸与无声重复“哺-哆”结合起来, 在入息时想着“哺” 、在出息时想着“哆”。不要让杂念干扰你的工作。这是在练习对于当下的知觉, 因此要保持警醒、全神贯注。“念住”逐渐确立之后, 心就不再去注意各种有害的想法与情绪。它会失去往常那股热衷感。既然不再走神了,它就会进入越来越深度的宁静。同时,一开始关注呼吸时, 它比较粗糙, 逐渐会越来越精细。呼吸甚至可能从知觉中彻底消失。它如此微妙精细,因此淡出不见了。那个时候呼吸不存在了, 只留下心本身的知觉。我选择的是“哺-哆”禅定(佛随念)。我从下决心的那一刻起, 就不曾让心离开“哺-哆”的重复。 我从一早醒来、到夜里睡下,迫使自己只想着“哺-哆”。 同时不去理会进步、退步。 禅修有进步, 我跟着“哺-哆”; 有退步, 也跟着“哺-哆”。不管怎样,“哺-哆”是我唯一的专注目标。对其它事情我毫不关心。保持这样一心一意的专注并不容易。我实在必须强迫自己每时每刻、不受干扰、与“哺-哆”结合在一起。无论我坐禅、行禅、作日常杂务,“哺-哆”始终在心的深处回响。 我秉性刚毅、毫不妥协, 这个性格对我的修法是有利的。 结果, 我全心全意投入修行,什么也不能动摇我的决心; 没有什么杂念能把心与“哺-哆”分开。一天又一天地这样修, 我总是确保“哺-哆”与即刻当下的知觉一起和谐共振。不久, 我开始看见, 宁静与专注从心的基本知觉中升起。那时,我就开始看见了心的微妙精细的本质。 我越使“哺-哆”往内走, 心越精细, 直到最后, “哺-哆”的精细与心的精细, 融为一体,成为同一个知觉本身。 我已不能把“哺-哆”从心的细微本质中分离出来。 我尽管试,就是不能令“哺-哆”从心里出现。通过勤奋与毅力, 与心如此密切结合,“哺-哆”不再出现在我的知觉中。心达到如此安详静止、如此精深的地步, 什么也不能在那里得到响应, 连“哺-哆”也不能。这个禅定阶段,类似于前面提到的呼吸消失阶段。这个情形发生时, 我不知所措了。原来以为, 整个修行过程必须紧紧抓住“哺-哆”。现在“哺-哆”不再出现, 我把注意力集中在哪里呢?到现在为止, “哺-哆”一直是我的主要依止。现在它却消失了。无论我怎样试着恢复这个焦点, 它还是消失了。我陷入了困境。唯一剩下的是内心深度的知觉本性, 一种清净、简单的知觉, 又明亮又清澈。那个知觉内部,没有什么实体可供攀缘。那个时候我理解了, 在意识、也就是知觉, 达到如此精深的状态时, 什么也不能入侵心的知觉领域。我既失去了“哺-哆”, 只有一个选择:我只得把注意力集中在当下这个无处不在、又凸显而出的知觉感。意识并没有消失, 相反,它无处不在。我过去把全部念注固着在重复“哺-哆”上,现在转而把它固着在宁静而专注的心里这个极其精细的知觉上。我的注意力始终固定在精细的知觉本身, 一直到后来, 它的凸显淡化了,我恢复了平常的意识状态。回到平常的意识状态后,“哺-哆”又重新出现了。 于是我立刻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在佛随念上, 不久, 每天的修行出现了一个新的节奏:我一心专注于“哺-哆”, 直到意识分解, 进入知觉的清澈、明亮状态, 然后沉浸在精细的知觉里, 一直到恢复常态, 然后加紧用功,再专注于重复“哺-哆”。 就是在这个阶段, 我的修持第一次获得了坚实的基础。从那以后, 修行不停地进步, 再也不曾有过退失。每过一天,心越来越宁静、安祥、专注。过去一直令我苦恼的修行起落感, 如今不再是问题了。 扎根于当下的“念住”, 取代了对个人修行状态的担忧,这个“念住”极其有力,与过去未来的想法已不再兼容。我的活动中心就是即刻当下-也就是每一次默念“哺-哆”的升起与消逝。我对其它事情毫无兴趣。结果我确信:过去的错误在于没有把注意力聚集于禅定用词。我那时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内在知觉这样泛泛的目标之上,没有一个明确目标, 各种念头闯进来, 很容易让心走失。我一旦理解了禅定初级阶段的这个正确方法, 就全心全意地修, 不让“念住”出现哪怕一瞬间的空隙。从早上醒来、到晚上入睡,我在清醒的每时每刻都在修。那样做起来是很难的,需要绝对的专注和毅力。我不敢放下警觉、不敢有一分一秒的松懈。就这样专心致志地使“哺-哆”进入内心,根本不去注意周围发生的事件。我的日常生活模模糊糊地过去了, 然而“哺-哆” 却始终焦点清晰。 我对这个禅定忆念词全心全意。 有了这个牢固的基础,心的宁静与专注练得不可动摇, 像山一样坚定不移。最后, 这个磐石般坚固的心智状态, 成了“念住”的主要集中目标。 随着心不断地获得内在的稳定感, 越来越凝聚起来,禅定用词“哺-哆”逐渐从意识中淡出了, 留下心的知觉在宁静与专注之下, 独自凸显。到了那个阶段, 心已经进入了“奢摩他”——这是一个高度集中的意识状态。 这个状态是独立的,与任何禅定技巧无关。知觉完全处在宁静、专注之中, 它本身成了注意力的焦点, 这个心态如此突出、有力,没有什么能升起推倒它。这就称为心处在连续的奢摩他中。换句话说, 心就是奢摩他, 两者等同了。从禅修的精深程度上讲, 禅定的宁静状态与奢摩他状态之间, 是有根本区别的。 摄心入定,在那个状态保持一段时间, 之后退回到平时的意识状态, 这叫做禅定的宁静状态。这样的宁静与专注是暂时的,只存在于心处于静止状态下的那段时间里。等到平常意识回转, 这些特殊状态就渐渐消散了。但是, 随着行者越来越熟练, 一次又一次地出入这个宁静、专注的状态,心就开始建立起一个牢固的内在基础。当这个基础在任何状态下不可动摇时, 就称为心处于连续的奢摩他状态。从此以后,即使心离开了禅定的宁静, 它依然感到坚固、紧凑, 好像什么也不能动摇它的内在焦点。与奢摩他始终结合着的心, 总是四平八稳、不受干扰。它感到彻底满足。由于这种内在结合极其紧凑、专注,日常生活的想法与情绪已经不再对它有什么影响了。这个状态下,心没有欲望去想任何事。它完全平静、满足、什么也不缺。在这个连续的奢摩他状态下, 心变得极其有力量。过去心渴望着经历思想与情绪,如今视它们如麻烦, 要转身躲开。过去的心如此焦躁不定, 即使想停下来, 还是不住地思考、想象什么。如今的心, 习惯于处在奢摩他状态, 没有思考任何事情的欲望了。它把念头当成不受欢迎的麻烦。当心的知觉始终凸显时, 它高度内向专注,不能容忍任何干扰。因为有这样高等的宁静, 奢摩他容易诱使心停驻在这个宁静的满足感中, 那些达到连续奢摩他状态的人,倾向于强烈执着于这个状态。心就一直保持在这个状态下, 只有修行达到以智慧为主时, 那时的结果就更满意了。
从那时起, 我对于修行更用功了。正是在那时, 我开始整夜坐禅, 从傍晚坐到天明。有一天晚上,我如往常一样朝内入定。因为有了良好、坚固的基础, 心轻松地进入了“奢摩他”。 只要心在那里宁静地休息,就不会意识到外在身体的感受。但是许多小时之后, 我出定时, 开始恢复全面感觉。到后来, 全身剧痛起来, 简直难以忍受。心里勇气顿失,那个良好坚固的基础瓦解了。全身的剧痛使身体发抖。就这样, 我开始了一场徒手格斗, 它使我对一个重要的禅修技巧有了洞见。那一夜不期产生这样的剧痛之前,我从来不曾坐过一整夜。我从来不曾下过那样的决心。我只是照常坐禅。但是当剧痛快要压倒我时, 我就想了: “嘿, 发生了什么?今晚我一定要下功夫把这个痛感弄明白。” 于是我郑重下决心, 不到天明不起身。 我一定要调查痛感的本质,直到获得清楚明确的理解为止。我要深刻地挖掘原因。有必要, 为了找到痛感的真相不惜失去性命。智慧开始积极着手解决问题。在我走投无路之前, 从不曾想到智慧可以这样敏锐。 它不停地工作, 如旋风般地移动着, 探索痛感的根源;它带着勇士的坚定, 决不后退、 决不接受失败。这个经验令我确信, 在真正的危机关头,智慧能够站出来迎接挑战。我们的命运不会注定是无明, 真的被逼到无路可走时,我们一定能找到帮助自己的办法。我那天就是这样。我被剧痛逼得走投无路时, “念住与智慧”立刻开始深入探索痛苦这个感受。痛感一开始沿着我的手背、脚背出现, 象撒上的热灰, 不过那还算是轻微疼痛。等它达到十成足时, 全身痛得象火烧一般。 全身的骨头、关节,像是在给痛感火上加油。 感觉好似每根骨头都碎了, 颈骨快要折断, 头将落地。身体各个部分同时痛起来时, 那个痛感之烈,简直不知怎么抵挡一下, 让自己喘一口气。在这个危机之下, “念住与智慧”没有其它选择, 只有深入痛感, 找到最痛的那个部位。“念住与智慧”就在痛感最强之处探索、调查,试着把它分离出来、看个明白。 “这个痛起源在哪里? 是谁在感受痛? ” 它们对身体每一个部位提出这些问题, 结果发现,身体每一处都保持着自己的属性。皮就是皮、肉就是肉、腱就是腱, 等等。 从出生以来一直这样存在着。另一方面, 痛感却与皮肉不同,它只是偶尔出现, 并不长期存在。一般情形下, 痛感与身体似乎总是绑在一起。但它们真是那样吗?集中注意力朝内看, 我注意到, 身体的每个部位, 都是一个物质现实。而物质是不灭的。但是我在寻找身体痛感的实质时, 发现有一处剧痛感,超过了其它各处。假如痛感与身体是一回事, 而身体各个部位是同样的现实, 那为什么一个地方的痛感比另一个地方更强烈呢?于是我试着把痛的各个侧面分离出来。“念住与智慧”是观察时不可缺少的。它们必须扫过疼痛的部位, 之后飞快地转向痛感最剧烈的部位,努力把感受与身体分离开来。在审视了身体之后, 它们很快把注意力集中到痛感, 接着又转向心。身体、痛感、和心智三个方面,就是这场调查的主要对象。尽管身体的痛感突出而强烈, 我看见心却保持着宁静感、不受影响。 无论身体何等不适, 心却并不难受、焦躁。这一点激起了我的兴趣。一般情形下, 杂染与痛感的力量汇合起来, 这个同盟导致心受身体之苦的扰乱。这个现象,促使智慧去探索身体的本质、痛感的本质、心的本质, 直到能够把这三个对象, 清楚地当成三个分列的现实来感知,每一个对象在自己的天然领域里都具有真实性。我看得很清楚: 是心把感受定义为“痛苦与不悦”。否则痛感就只是一种自然现象。 它并不是身体的内在组成部分,也不是心的内在组成部分。对这个原理, 一旦了解得绝对清楚, 痛感立刻消失了。那时, 身体仅仅是身体,有着自己独立的现实存在。痛感仅仅是感受, 一刹那间那个感受直接闪入心中。 一旦痛感闪入内心,心就知道痛苦消失了。它消失得无影无踪。此外, 整个身体也从知觉中消失了。那个时刻, 我的意识中丝毫感觉不到身体。 只有一种简单而和谐的知觉独自存在。没别的了。心如此精细,不可描述。它只是知觉——有一种精深的内在知觉遍布一切。身体感彻底消失了。尽管身体还在坐禅,我对它完全没有知觉。痛感也消失了。没有留下一丝一毫的物质感。只剩下心的知觉。一切思考终止了; 心不再形成一思一念。 思考终止时,内在的静止就不受丝毫的动态干扰。心独自定驻不动。由于“念住与智慧”的力量, 体内火烧刀割般的痛感彻底消失了。甚至我的身体也从意识中消失了。知觉独立存在着,好象挂在半空中。它完全是空的, 但同时又有着敏感的知觉。因为组成身体的元素不再与心相互作用,心就不再感知它的存在。这个知觉是一种纯净、独立的意识, 不与任何事物相连接。它极其宏伟壮观、令人敬仰。这个经历实在奇妙、难以相信: 痛感彻底不见了。 身体也消失了。 只有知觉没有消失, 它如此精细、微妙, 难以描述。我只能说,它出现了。那真是一个奇妙的内在状态。心的内部没有活动, 最细微的波动也不曾泛起。它就那样长久沉浸于静止之中, 直到后来,它从“奢摩他”退出时, 片刻之间泛起波动, 接着又静止下来。这个波动是自发的。不可能有意产生。任何意念会把心立即带回常态。心沉浸于静止之中, 等到满足之后,就开始搅动起来。它知道有一个涟漪片刻升起、 消逝。过一段时间, 又有一个涟漪升起、即刻消逝。渐渐地,波动变得越来越频繁。当心已经与奢摩他的根基(the very base of samadhi)凝聚在一起时,它的撤离并不是一步完成的。 这点我看得很清楚。心微微荡漾, 意味着有一个行蕴(sankhãra)升起片刻,在能辨识之前就消失了。它波动起来、又消逝了。 一次又一次, 波动升起、消逝,频率逐渐加快,直到心最后回到常态。这时候我才开始对身体有了感觉, 但是仍然没有痛感。 开始我一点不觉得痛, 只是慢慢地,痛感又重新出现了。这个经历, 给了我不可动摇的确定感, 增强了我内心的精神基础。我发现了与痛感抗争的基本原理: 痛感、身体、和心是完全分开的现象。但是,正因为有“痴迷”这个心理杂染, 三者汇合为一体。“痴迷”如同慢性毒药,渗透心智、污染我们的感知、扭曲真相。痛感只是一种自发自然的现象。但是,当我们抓紧它,当它是一种烧灼般的不适感时,它立刻火烧火燎起来,因为我们对它作了那样的定义, 令它具有烧灼感。过了一阵, 痛感恢复了, 于是我不能休息, 必须重新对付它。象先前禅观一样, 我又深入探索这个痛感。不过这一次,我不能使用前次的调查技巧, 尽管那个方法效果极好。然而, 过去使用的技巧却与当下不再有关。为了与内在事件的发展保持同步,我需要新鲜的技巧、需要通过“念住与智慧”, 根据当前情况, 相应地重新设计。痛感的属性还是一样,但是探索技巧必须适应当下情形。哪怕我已经成功地用过一次, 却不能抓紧旧的调查技巧, 来对付新情况。必须有新鲜、创意的技能,在实战中根据当下情形进行设计。于是“念住与智慧”又重新开始工作, 不久心又与奢摩他的根基汇合了。那一晚, 心就这样汇合了三次, 每一次我都得进行徒手格斗。第三次后, 天亮了,决定性的抗争也结束了。心变得大胆、鼓舞、无畏。对死亡的恐惧, 在那天晚上终止了。痛感只不过是自然现象, 它在轻与重之间不住起伏。只要我们不把它们当成个人负担, 它们对心就没什么特殊意义。痛感本身,并没有什么内在含义, 因此心不受影响。身体本身, 也没有什么内在意义, 它并不为感受、自我, 添加什么意义-当然了,除非心给身体赋予特殊意义, 把由此而产生的苦收集起来, 自己烧自己。外在条件实际并不造成我们的苦, 只有心在造苦。
那天早晨起身时,我感到不可言喻的大胆、果敢。我对这个经历感到惊奇。过去修持中从来不曾发生这样的事。在我进行了彻底、勤勉的观照、探索之后,心已经完全切断了对一切客体的关注, 带着真正的勇气朝内汇集, 凝聚成了那个壮观的静止。出定时, 它依旧带着不怕死的勇气。我现在知道正确的探索技巧了, 可以肯定下次痛感再出现, 也不惧怕了。那些痛感说到底,都有一样的属性。身体是同一个。 智慧也同样是我的能力。因此我对于痛感与死亡无所畏惧。一旦智慧对于哪些死、哪些不死的真相有了知觉,死亡就成了一件很平常的事。头发、指甲、牙齿、皮肤、肌肉、骨胳: 它们都会回归原始的元素形态, 它们只是土元素。土元素什么时候会死呢?它们分化瓦解时, 变成什么呢? 身体的一切组成部分, 终究会回归原始属性。土与水会回归元素本性,风与火也一样。没有什么会消亡。那些元素只是集结起来、形成一堆, 接着心就住了进来。“心”是迷幻大师, 它进驻之后,让这堆元素活动起来, 让它有了一个“自我”的身份, 接着就背起了这堆重负。“这是我, 这属于我。” 心把这一整堆物质指称给自己,积累起无穷无尽的痛与苦, 带着错误的假设, 自己燃烧自己。“心”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不是那一堆物质元素。身体并不是什么带着敌意的东西, 起伏不停地威胁我们的安宁。它是一个独立的现实,随着内在条件在作自然变迁。只有对它的行为作了错误的假设, 它才成了负担,我们不得不背负起来。那才是我们苦于身体痛感与不适的原因。身体本身并不造苦, 苦是我们自己造的。就这样, 我清楚地看见,没有什么外在条件能使我们产生苦。是我们自己对事物有错觉, 那个错觉升起了痛苦之火, 困扰我们的心。我清楚地理解了, 没有什么会死。心肯定不死, 实际上它越来越凸显出来。我们越是彻底探索四元素, 解析分离出它们的原始属性,心越明显地独立出来。 那么死亡在哪里呢? 死的又是什么呢? 四元素-土、水、风、火-它们从来不死。那么心怎么会死呢?它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有知觉、越来越有洞察力。这个根本知觉从来不死, 那么为什么它怕死呢? 因为它自己骗了自己。多少劫世以来,它一直欺骗自己, 相信死亡的存在; 实际上从来没有什么会死。因此,当痛感在体内升起时, 我们必须认识到, 它只不过是感受, 没有别的了。不要从个人角度定义它,不要假设这是对你发生的事。从你出生那天起, 身体就有了痛感。从母亲子宫里出生时,你经历了剧痛。人只有经历这番磨难才能出生。痛感从那时起就存在了, 它是不会回过头来, 改变属性的。身体的痛感总是表现出同样的基本属性:升起、暂住、消失;升起、暂住、消失-就这么多。
要探索体内升起的痛感, 获得对于它们的如实知见。身体只是一类物质形态, 你从出生以来就熟悉了它。但是, 当你相信你就是身体,相信你的身体有痛感时, 你就处在痛苦之中。身体、痛感、知觉被等同起来, 合为一体:你的痛苦的身体。身体的痛感来自于某种机体故障。它的升起与身体某些方面有关, 但它本身却不是物质现象。对于身体和感觉的意识,来自于心——它才是知觉者。但是, 当这个知觉, 错误地理解了痛感, 担心起痛的原因和表面上的剧烈程度,就升起了情绪上痛苦。痛感不只有痛, 还说明你和你的身体哪里坏了。除非你能把这三个独立的现实分离开来, 身体的痛感,总会造成情绪上的苦恼。身体只是一种物质现象。无论我们对它怎么看, 也不会改变真相的原理。身体的真相就是这样一个物质存在。四元素属性, 以某种形式组合起来,构成了被称为“人”的东西。 这个身体, 被指定为男人女人, 还被赋予了个别的名字与社会地位, 但本质上它只是色蕴(rupakhandha)——也就是物质聚集体。各个组成部分堆在一起,构成了人体这个独特的物质现实。每个身体结构是那个现实的组成部分。四元素可以以许多不同的方式组合。 在人体中,我们会谈到皮肤、血肉、腱骨、等等。但是不要因为它们名字不同, 就受骗了, 以为它们是分开的现实,要把它们看成同一个根本现实-也就是物质聚集体(色蕴)。“感受”这个聚集体(受蕴),它们存在于自己的区域。它们不是身体的一部分。身体也不是感受。它在身体的痛感中没有直接作用。色蕴与受蕴这两种蕴, 比起辨忆(想蕴),思维(行蕴)和意识(识蕴)这几个蕴, 要更为显著, 因为后面三种蕴升起后即刻消失,因此看见它们要难得多。但是感受在消失前,会保持片刻。因此受蕴比较明显, 在禅定中容易分离出来。痛感升起时, 要直接把注意力集中在那里, 努力去了解它们的真相。要迎头面对这个挑战。不要转换注意力避开痛感。也要抵制希望痛感消失的诱惑。调查的目的:必须是寻求真正的理解。而痛感的消解,只是了解真相之后的“副产品”,不能把它当成主要目标。那样做, 在止痛的愿望不得实现时, 只会成为精神烦恼的更大苦因。面对剧痛强自忍耐,也不会成功。把注意力单单专注于痛感, 而不去观察身体与心, 也不会成功。为了获得正确的结果,这三个因素都必须包括在探索过程中。探索必须始终直观、有目的。
世尊教导我们,探索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把一切痛苦只看成一种升起、短暂持续、消逝的现象。不要牵扯在其中。不要把痛苦看成个人的、与自己不可分开的一部分,因为那样做正是逆着痛感的真相而行。那样做也会破坏探索痛感的技巧、阻止智慧对痛感真相的理解。不要凭空给自己造麻烦。在观察痛感的每时每刻时,要看见真相,观察它的暂时性与消逝性。痛感实际上就那么多。你用“念住与智慧”, 把痛感分离出来后, 就把注意力转向心, 把“感受”与“内在的知觉”相比较,看看它们是不是真的不可分离。再转过来,把“心”与“身体”进行同样的比较,看看它们到底在哪方面相同? 要明确地集中于一个目标, 在调查某一点时不要走神。你就只专注一个方面,比方说, 把全副注意力放在“痛感”上, 对它进行分析,直到你理解了它的特点之后, 再转过来观察“心”, 努力观察知觉的特点。这两个是不是相同? 去比较它们。“感受”与“了解感受的知觉”,是同一件东西吗? 是什么原因使它们这样? 那么,“身体”与“心”有类似的特点吗?“身体”与“感受”一样吗?这三个方面是不是类似到了可以捆作一堆?身体是物质, 它怎么会和心相似呢? 心智是精神现象, 是一种知觉。组成身体的物质元素本身没有知觉,没有了解能力。土、水、风、火四元素, 什么也不知, 只有精神元素(manodhatu)有知觉。 既然这样,心的知觉本性与身体的物质元素, 又怎么能等同起来。它们显然是不同的现实。同样原则也适用于痛感。它没有内在知觉、没有了解能力。痛感是自然现象, 升起时与身体有关, 但它并不了解身体的存在,也不了解自身的存在。痛感依靠身体作为它的物质基础。没有身体,它们不可能产生。但是痛感本身却没有什么物质上的现实。人们把随着身体升起的各种感觉, 当成与身体的有关部位不可区分。人们本能地把“身体”与“痛感”等同起来, 于是就好象身体本身在痛。我们必须纠正这个本能的反应;纠正的办法:是探索痛感作为感觉现象的特点, 再去探索感到剧痛的那个身体部分的纯粹物质特点。这样做的目的是,对某个身体部位,比方说膝关节, 要清楚地进行判断, 看它本身是不是表现出痛感的特点。它们具有什么样的形状与姿势?“感受”并不具有形状与姿势。它们只是一团无形的感意。而身体却有特定的形状、有内外颜色,并不因感受而变动。它的状态与痛感升起前一样。物质不可能因为有痛感的改变, 因为痛感, 作为一个独立现实, 对物质没有直接影响。比方说,膝盖痛、肌肉痛: 膝与肌只是由骨、腱、肉等组成。它们本身不是痛。尽管两者处在一起, 却各有各的属性。心同时了解这两个方面,但是由于知觉受到“痴迷”的蒙蔽, 自动假设:痛感存在于组成膝盖的骨、腱、肉上面。出于同样的“根本无明”,心假定身体的所有方面, 都属于个人存在感的一部分。因此痛感也与个人的存在感绑在一起。“我的膝痛。我有痛苦。我不要受苦。我要痛感走开。” 这个“想赶走痛感的欲望”是一种杂染, 它把身体的感受, 转成情绪上的苦,于是就扩大了不适的程度。痛感越强, 想驱除痛感的欲望越大, 于是就导致更大的精神烦恼。这些因素不断地相互推动。因此, 由于自己的无明,我们背负起苦的重压。为了把“痛感、身体与心”看作分离的现实, 我们必须从正确的角度观察各个方面。从这个角度去看, 三方面自行发展,却不会汇集成一体。平时它们绑在一起,成为自我形象的一部分, 不存在独立观察的立足点, 因此没有办法把它们分开。只要我们坚持把痛感当成是个人的, 就不可能突破这个僵局。当五蕴与心融为一体时, 我们没有行动余地。但是,当我们带着“念住与智慧”进行探索, 在它们之间来回观察, 对每一个方面的特点进行分析、比较时, 我们会注意到它们之间有着明确的区别,从而能清楚地看见它们的本质。它们各自作为独立的现实而存在。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随着内心悟透了这个深刻的原则,痛感就开始减少、淡化、消失。同时我们意识到:“痛感的体验”与“抓紧它的自我”之间存在着根本关系。那个关系立足于心内部, 朝外伸展出来,包括了痛感与身体。真正对痛的体验, 发自于内心、发自于心中根深蒂固的“我执”, 是这个“我执”对身体痛感产生了情绪痛苦。我们要始终保持完全的知觉, 跟着痛感朝内走, 寻找它的来源。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痛感时, 所调查的那个痛感就撤退了,逐渐退回到心里。我们一旦毫不含糊地意识到:实际上是“心的执取”导致我们把痛当成是个人烦恼, 那个痛苦就消失了。它可能会完全消失,只留下心的知觉。或者,痛感的外在现象依然存在, 但是由于情绪上的执取已经无效, 就不再感觉苦了。它是心以外的不同的现实,两者不再相互作用。从那一刻起, 心停止了对痛感的抓取, 一切联系就给切断了。剩下的是心的精髓、也就是知觉, 在五蕴之痛中,宁静不受干扰。无论当时痛感有多严重, 怎么也不能影响心了。一旦智慧清楚地意识到, 心与痛感各自真实, 这种真实却相互独立, 两者就根本不会相互影响了。身体只是一堆物质。痛苦升起时的身体,与痛苦消失时的身体是同一个。痛感并不改变身体本质; 身体也不影响痛感本质。心了解痛感升起、暂住、消失。但是心的真正知觉本身,并不象身体和感受那样升起消失。心的知觉是稳定恒常的。既然有这样的理解, 痛感无论何等剧烈, 对心不会有影响。 剧痛升起时,你甚至能够微笑——你能够微笑!——因为心是独立的。它的知觉不间断, 但是不牵扯到感受之中, 因此就不苦。这个层次, 要通过“念住与智慧”的精进努力才能达到。这个阶段是“智慧培养奢摩他”。并且, 由于心已经通过观察各个方面,获得了彻底理解, 就在那个时候, 达到了圆满的奢摩他。心带着难以描述的大胆与精细聚焦起来。这个惊人的知觉, 来自于对事物进行穷尽分析之后从中脱离。一般情更新于:2023-05-22 12: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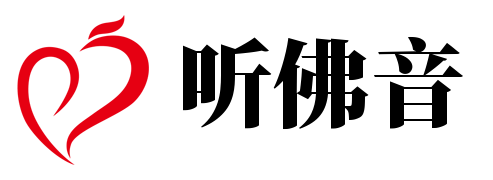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