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希那穆提日记(20)
摘自《克里希那穆提日记》
1973年10月6日
这片翠绿的田野上,突兀地长着一棵大树,它占据着整块地方;这是棵古树,山上所长的其它树都对它表示崇高的敬意。在它独处的时候,俯视着欢腾的溪流,山丘以及小木桥对面的农舍。你经过这里时,心里怀有对它的赞美之情,而当你回来再见它,是带着一种更从容的心情。它的树干很粗大,深深地扎根在地上,显得坚实和不可摧毁;它的分枝很长,深褐色,弯弯曲曲;给地面投下充足的遮蔽。夜晚,它回到其独处的本色,不太愿意别人靠近,但在白天的时光里,它却是开放着,欢迎你的到来。这是一棵完整的大树,没有经受过斧和锯的伤害。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坐在树下,你会感受到令你肃然起敬的它所走过的岁月,又因为你独自地和它在一起,所以你意识到它生命的深度和美。
那个年迈的村民疲惫地从你身边走过时,你正坐在木桥上眺望着黄昏的落日;他几乎又双目失眠,跛着脚,一手提着一捆东西,另一只手撑着一把拐杖。那一个傍晚,夕阳的光彩普照在每一块岩石,每一棵树木和每处的灌木上;草地和田野的色彩似乎是自己发出来的光。太阳已落下一座圆型的山后,在这些缤纷灿烂的晚霞里,晚星出现了。那个村民在你面前停了下来,注视着这奇异的色彩,然后望了望你。你们互相望着对方,没说一句话他迈着沉重的步子向前走去。这是种友好的,亲切的,怀有敬意的交流,不是那种无聊的敬意,而是很虔诚的。那一瞬间,时间和思想都不复存在。你和他处在一种完完全全的虔诚里,不为信仰,偶像所玷污,亦不为言语或贫困所玷污。那条石丛间的山路上,你不时地与对迎面走来的人擦身而过,每次当你抬头彼此相望,露出发自内心的喜悦。
他和他的夫人,正从对面的寺庙走来。彼此默默无语,被唱诵的经文和礼拜所深深打动。你刚巧走在他们的后面,被他们的敬意,他们决定要过一种宗教生活的力量所触动。但是,当他们的孩子跑向他们,他们被引向对孩子的责任时,这一切便很快会消失。他有某种职业,也许他很能干,因为他有一个大宅子。生活的重担会压垮他,虽然他常常会去寺庙,可是冲突还会继续。
文字不是事物,偶像,符号不是真正的实体,实体不是文字。将实体变成文字再将它擦除,错觉便发生了。智力也许排斥意识形态、信仰的整个结构,以及伴随它们的所有装饰和力量,但是理性会辩析所有的信仰和概念化。理性是思想的秩序,而思想是外在的反应。因为思想是外在的,思想将内在整合起来。没有人可以只存在于外在,而内在成为一种需要。这个分离是产生“我”和“非我”的基础。外在是宗教和意识形态的神;内在试图与那些意像相符合,冲突便开始了。
其实无所谓的“内在”和“外在”,只有整体。经验者就是被经验的。分裂就是错乱。整体性不仅仅是文字的表达;当“外在”和“内在”的分离完全地消失后,整体便存在了。
忽然,当你独自走着,没有一丝的思绪,只有去掉观察者的观察,你开始意识到某种神圣,某种思想永远无法构思出来的神圣。你停下脚步,你观察树,观察鸟,观察走过的人;它再也不是幻觉或是思想欺骗自己的什么。它就在你眼中,就在你整个生命中。蝴蝶的色彩就是蝴蝶。
夕阳产生的色彩在褪去,夜尚未完全降临,在夕阳还没有完全落下山后,羞怯的新月已露了出来。
1973年10月7日
一场山雨持续了三、四天,带来了凉爽的天气。地面混漉漉的,十分的泥泞,所有的山路都非常的滑,小溪从徒峭的山彼流下,梯田里的农活都已经停顿下来。林木和茶园烦透了这般的水气;已有一个星期没见阳光了,天气颇为寒冷。山脉位于北面,露出高耸的山峰和覆盖着的皑皑冰雪。寺庙周围的旗子在雨中垂丧着,失去了以往的喜气,风中舞动时的欢快色彩也不见了。电闪雷鸣,在山谷回荡,一层厚雾遮住了锐利的闪电。
次日清晨,天空湛蓝,十分的柔美,高耸的山峰,一派静默,显示永恒的气息,在清晨的阳光下熠熠生辉。村子和高山之间是一处深谷,弥散着幽蓝色的雾气。一直向前,晴空中高耸着的便是喜玛拉雅山脉第二高峰。你几乎可以触手可及,但它却离你有几英哩远,你忘记了距离,因为它就坐落在那,它巍峨的气势是如此绝然的完美和不可测量。快要中午时,它消失了,隐没在山谷渐渐变暗的云层里。只有在清晨时它才显现,然后几小时后便又消失了。难怪古人会期望在这些高山上,这些雷声和云层中有神灵显现。为他们生活祈福的神祇深藏在这些无法接近的雪山上。
他的弟子前来邀请你去拜访他们的上师,你礼貌地谢绝了,但是他们经常会来,希望你会改变主意或接受他们的邀请。对他们不懈地邀请你渐渐厌烦了,于是他们决定由他们的上师带上几名他选定的弟子来拜访你。
这是一条吵杂的小路,孩子们在那玩板球,他们有一个球板,而球则是用几块零星的砖头替代。他们叫啊,笑啊,尽情地在玩着,只有当汽车经过时才停顿下来,司机也在专神看着他们的玩法。他们会这样日复一日的玩下去,只是那天早晨当上师带着他那把小巧的,发亮的拐杖前来的时候,他们玩得尤为起劲。
上师进来的时候,我们几个正坐在铺有薄垫子的地板上,我们于是起立给了上师一块垫子。
他盘腿而坐,将他的藤制拐杖放在前头,那个薄垫子似乎给予他一种很权威的姿式。他已找到了真理,经验到真理,这位已知的他,在向我们打开真理之门。他说出的话,对他或对别人都是金科玉律,你只是一位探索者,但是他已经到达了。你在探索中也许会有迷失,他可以帮助你,用他的那套方法,但是你必须顺从。你平静地回复,所有的寻找和发现都毫无意义,除非心灵免受制约,自由是最初和最后的步骤,心灵服从于任何权威,好比在捕捉错觉,而行动产生悲愁。他用怜悯的眼光看着你,时而露出关切的目光,时而露出恼怒的眼神,仿佛你是个疯子。然后他说:“最伟大和最终的经验已传给了我,没有探索者能够拒绝它。”
如果实相或着真理是可以被经验的,那也仅仅是你自己心灵的投射。被经验的不是真理,而只是你自己心灵的创造物。
他的弟子开始坐立不安。信徒毁了他们的导师,也毁了他们自己。他起身告辞,后面跟着他的弟子。孩子们还在街上玩着,有人被罚下场了,传来他们的掌声和欢叫声。
真理无路可寻,不论是历史地,还是宗教地去寻找。真理不是经由辩证法去经验或是去发现的,也不是见之于转换见解和信仰中。当心灵从已知的一切事物中解脱出来,你便会见到真理。那个壮丽的山峰也是生命的奇迹。
1973年10月8日
那个安静的早晨,猴子随处可见,在游廊,屋顶甚至是芒果树上,到处是成群的猴子;它们是脸褐红色的那种。小猴子在树上互相追打,离它们的猴妈妈不远,那只体形大的公猴独自坐着,注视着整群猴子,它们的数量一定有20只之多。它们很具有破坏性,当太阳高高升起后,他们才慢慢地消失在林子的深处,远离人类的住所。那只公猴是第一个离开,其它的猴子安分地跟着离开。接着,鹦鹉和乌鸦回来了,开始它们惯常的叽哩喳啦,以表明它们的存在。其中有一只乌鸦特别会叫,不论是在做什么,总带着它那沙哑的声音,通常是在相同的时刻,开始其没完没了的叫声,至到被驱散为止。日复一日,它会重复这种表演,它的叫声能深深地穿透房间,不知咋的,当它叫声一起,其它的噪音似乎就此消失了。这些乌鸦为避免它们之间剧烈的争吵,行动敏捷,非常机警,这对他们的生存是很有效的。猴子似乎不喜欢它们。今天将会是一个美好的日子。
他是一个清瘦但精壮的人,头型很好看,眼睛总挂着微笑。我们坐在罗望子树荫谅处的长凳上眺望着河水,这棵树是许多鹦鹉和一对仓鸮鸟的家园,在清晨的阳光里它们在晒日光浴。
他说:“我化了许多年在静坐上面,控制我的思想,饮食,一天只吃一餐。我以前是个社会工作者,当多年以前我已放弃这份工作,因为我发现这个工作无法解决人类深层次的问题。仍有许多人在从事这样的社会工作,但是我不再对它有兴趣了。对我而言,去理解静坐的完整意义和它的深度更重要些。各类静坐的学派都提倡某种形式的控制,我练习过不同的门派,但怎么说呢,似乎总没有尽头。”控制包含有分裂即:控制者和被控制事情的分裂,这种分裂就像所有其它的分裂一样,给人的行动和行为带来冲突和扭曲。这种片断化是思想的运作,一个片断试图控制其它的部分,你可以将这种片断称为“控制者”或别的什么名称。这种分裂是人为的而且非常有害。事实上,控制者就是被控制的。思想从其本质上讲是断断续续的,因此这就会产生混淆和悲愁。思想已将世界分裂成大大小小的国家,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宗教派别。思想是记忆、经验和知识储存在大脑里的反应,只有当大脑在安全和有序的情形下,它才能有效地、健全地工作。大脑为了在身体上存在下去,它必须免受任何的伤害,外界生存的必要性是容易理解,但心理上的生存就是完全另一回事了,它是思想整合起来的意象生存。思想将存在的事物区分成外在和内在,从这种分裂中,冲突和控制产生了。因为内在的生存,信仰、意识形态、神祇、国家、结论就成为不可或缺的了,由此也带来了数不胜数的战争,暴力和悲愁。对于内在生存的渴望,和与之相应的无数意象,是一种弊病,是不和谐的。思想是不和谐的。它的所有意象,意识形态,他的真理都是自我矛盾的,是具有破坏性的。思想除了它的技术成就外,不论是外在地还是内在地,它所带来的混乱和快乐很快会转为痛苦。去读懂所有这些发生在你日常生活中的,去倾听、去观察思想的运动这是静坐带来的变化。这个变化不是将“我”转变成伟大的“我”,而是意识内容的变化,意识是思想的内容。世界的意识就是你的意识,你是世界,而世界就是你。静坐是思想完全的变化,也是思想的活动。和谐不是思想的果实,它来自于整体的领悟。
清晨的微风已消去,就连一片树叶都纹丝不动,河水也开始完全的静了下来,河对岸的噪声穿越宽阔的河水传到这里。此时连鹦鹉都安静了下来。
1973年10月9日
你乘坐一列窄轨火车出行,火车几乎每站停靠,到处是叫卖热咖啡和茶,毯子和水果,甜食和玩具的小贩,他们卖力地兜喊着。睡觉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天亮时,所有的乘客都得乘船由浅海边渡海去那个岛上。那里的火车已等着带你去小岛首府,火车穿行在绿意盎然的乡间,你可望见窗外的丛林和棕榈树,以及茶园和村子。这是一片令人心旷神怡,充满欢喜的土地。靠海的地方天气又热又湿,但在山那边种植茶树的地方天气相当凉爽,空气里能闻到远古的气息,这里视野开阔,非常的纯朴。但在城里,就像所有的城市看到的那样,到处是噪声、污浊,贫困带来的脏乱和金钱的粗俗;码头那边,停靠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
房子位于一个隐蔽的地方,有一队人出来迎接他,向他献上花环和水果。一天,有一个人问他是否想去看一头幼象,很自然地我们要去看的。这是一头出生才二周的幼象,体形巨大的母象有些紧张,不时地看护着它,他们这样告诉我们。车子带着我们出城,经过脏乱和污浊的地方到达一条水面呈棕色的河,河岸边是一个村子;周围生长着高大厚重的树木。那头黑色的体形巨大的母象和他的幼象在那。他待在那有几个小时,至到母象习惯了他的存在。他必须经人介绍,准予去触碰母象那长长的鼻子,并给象喂了些水果和甘蔗。母象鼻子灵敏的末端要求更多的食物,于是在它的嘴里又放进了些苹果和香蕉。新生的幼象站在母象的二腿中间,小小的鼻子挥动着。它是那头体形大的母象缩小的翻版。最后,母象容许他触摸它的幼象;它的皮肤不是那么的粗糙,鼻子不停地在摆动,比其身上其余部分更可爱。母象一直在注视着,它的饲养员不得不时刻地让母象放心。这真是一只好玩的幼象。
女人走进小屋,非常哀伤。她的儿子在战争中阵亡。“我深深地爱他,他是我唯一的孩子;他受过良好教育,指望他将来会是心地善良,聪明能干的人。他死了,这样的不幸为什么要降临在他和我的身上?我们母子间是有着真真切切的情感和爱的啊。这是多少悲惨的事情啊。”她呜咽着,眼泪似乎流淌不止。她握住他的手,不一会她渐渐平息下来听他说话。
我们在孩子的教育上投下了无数的钱,我们含辛茹苦地照顾他们,我们变得深深地依赖于他们,他们充实了我们孤独的生活,因他们我们感到充实,感到血脉的延续。我们为何要受教育呢?是为了要成为科技的机器?是为了在劳动中过我们的日子,死于某种意外或得什么痛苦的疾病?这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宗教带给我们的生活。全世界每一个妻子或母亲都在痛哭,因战争或是疾病夺取我们的儿子或是丈夫。爱是依附吗?爱是泪水和丧失亲人的悲痛吗?爱是孤独和悲愁吧?爱是自我怜悯和分离的痛苦吗?要是你真爱你的儿子,他会看到你的儿子并没有死于战争。世上曾经历过数以千计的战争,可从来没有母亲和妻子完全拒绝导致战争的行为方式。在悲痛中你会哭泣,然而你还是支持导致战争的制度,虽然并非心甘情愿。爱确信非暴力。
那个男的在述说为什么要和妻子分离。“我们很年青时就结了婚,几年后事情在各方面变的糟糕起来,在性的方面,精神方面,我们彼此间似乎完全无法相融。虽然一开始时,我们互相爱着对方,但逐渐地演变成互相憎恨,分离是不可避免的,律师正在打理此事。”
爱是喜乐和欲望的持续吗?爱是肉体上的快感吗?吸引和满足就是爱吗?爱是思想的用品吗?爱是由某个特定事件所组合起来的东西吗?爱是相伴、仁善和友情吗?如是其中的任何一个占具优先的话,那就不是爱。爱就像死一样是最终的。
穿过林子,草场和开阔的地带,有一条小道通向高山。进山前,有一条长凳,一对老夫妇坐在那,望着阳光照射的山谷,他们经常到这里来。他们坐着没有言语,安静地望着眼前美丽的大地。他们在等着死期的来临。那条山道一直通往雪山。
1973年10月10日
雨来了又去,巨大的圆石块在早晨的阳光里闪闪发光。干涸的河床又充盈起水,土地重新焕发生机。土壤更加红润,所有的灌木和草叶更加翠绿,就连那些老根的大树也吐出了新芽。家畜在茁壮,村民们也不那么削瘦了。这些山丘和土地一样古老,巨大的圆石块似乎已被精心地与那儿的环境相和谐。向东的那处山丘,有一块颇似平台的空旷土地,正在兴建起一座方形的寺庙。村里的孩子要步行几英哩去学习读写;这里有一个小孩,独个儿的,一手拿着课本,一手拿着食品,满脸喜气地跑向邻村的学堂上学。我们走过时她停顿下来,露出了羞怯又好奇的眼神,要是她还不快走,怕要迟到了。田里的稻子长的格外的绿。这是一个漫长而祥和的早晨。
二只乌鸦在空中打闹,互相叫骂着,撕扯着,空中没有供它们立脚的地方,所以它们飞回到地面,继续着打斗。在地面上,羽毛开始飞扬,争吵变得激烈起来。突然,约有12只其它的乌鸦飞来袭击它们,这场打斗才告结束。在其它乌鸦不停地斥啧和叫骂后,它们消失在树林里。
暴力无处不在,它存在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存在于大多数没受过教育的人群;它存在于知识分子也存在于多秋善感的人群中。教育和有组织的宗教都无法驯服人类免于暴力,相反地,他们要对战争、对刑罚,对集中营和对陆上海上的动物被宰杀负责。人类越是进步,似乎也变得越加凶残。政治已变成强盗手段,派系纷争,民族主义导致战争;有经济战争、有个人的敌意和暴力。人类似乎并没有从经验和知识中学到什么,而各种形式的暴力仍在继续着。在人类和社会的转变过程中,知识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呢?
人类投入的精力用来知识的积累,并没有改变人类,也没有终止暴力。人类投入的精力用来解释一千次了的为什么人这样好斗、这样野蛮、这样麻木,也没有终止人类的残忍。人类投入的精力用来分析原因,人类为什么会丧心病狂的破坏、以暴力为乐、施虐狂、横行霸道的活动,同样也没有使人类变得深思熟虑和心善起来。虽然记载不少这方面的文字和书籍,威胁和报复,人类继续着自己的暴力。
暴力不仅仅表现在杀戮、轰炸、通过流血的***性的更替,暴力还表现得更加深层,而且更藏而不露。服从和仿效是暴力的迹象,强加和认同权威是暴力的一种表现,野心和竞争是这种攻击性和残忍性的一种表现,而攀比产生妒嫉所带来的仇恨和敌意。只要有冲突,不管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就有暴力存在的基础。形形色色的分裂导致了冲突和痛苦。
这些你都了解,你读过有关暴力的行为,你亲眼目睹发生在自己身上或是周围的暴力,你也耳闻暴力,然而暴力还是没有终止。为什么呢?各种的解释和分析暴力行为的原因都没有实际的意义。如果你沉湎于这类的解释和分析上,那你是将精力浪费在想要超越暴力上了。你要用你全部的精力去应对和超越正被用在浪费的精力上面。控制暴力是另一种形式的暴力,因为控制者就是被控制的。只有投入全部的精力,全然地去关注,各种形式的暴力才会终止。关注不是文字上的,它不是思想上的一个抽象的公式,关注是日常生活的一个行动。行动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但是假如行动是意识形态结果的话,那么行动也会导致暴力。
雨后,河水流过每一处巨大的圆石块,流过每一城镇和村庄,河水虽然被污染的很严重,它会净化自己,奔腾于山谷,峡道和草场。
1973年10月12日
又来了一位知名的上师看他。我们坐在一个可爱的有围墙的花园里,草地青翠被修剪得非常完善。花园里开有玫瑰花,香豌豆花,还有呈亮黄色的万寿菊和长在东北部的其它花卉。墙和树木阻挡着外面零星驶来的汽车噪声,空气里飘散着花卉的芳香。晚上,一群胡狼家族会从树下它们藏身的地方跑出来;它们已挖开了一个很大的洞,母胡狼和它的三个幼崽就住在里面。它们看上去非常健康,太阳落山后,母胡狼会带着它的幼崽出来,紧挨着树边。垃圾放在房子的后面,胡狼晚些时候会去那儿寻食。另外还有一拨猫鼬的家族,每个晚上,那个长着粉红色鼻子和一条长长粗粗的尾巴的母猫鼬会从它藏身之地出来,后面跟着它的二个幼崽,一前一后地,紧挨着墙。它们同样要潜行至厨房的后面,那里有时候为它们留着些食物。因为它们的存在,花园里没有蛇的侵扰。它们似乎从不和胡狼一家相遇,不过要是它们真的碰到了一起,彼此也会互不相扰。
上师几天前就已宣布,他想要来拜访。他先到达,他的弟子一个接着一个地紧随其后。他们会触摸他的脚,以示对他的敬仰。他们还想再触摸上师另一只脚时,但是他阻止了;他告诉他们这样有失体统,但是传统和他们对天堂的向往非常强烈。上师不入屋内,因为他发过誓再也不登已婚者的房屋。那天早晨,天空格外的蓝,拖着长长的阴影。
“你反对要做一位上师,但你是上师中的上师。我自你年青时候起便开始观察你,你所讲的是小部分人明白的真理。对大多数人而言,我们是不可或缺的,要不然他们会很失落;我们的职权就是挽救那些愚纯的人。我们是诠释者。我们有我们的经验,我们知道。传统是一个壁垒,只有极少数人可以独立地看见未经修饰的实相。你是深受尊崇的,但是我们必须和信众们一道走,唱他们的歌,景仰圣名,撒圣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是伪君子。他们需要帮助,而我们在那就给予那些的帮助。要是容许有人问,那种绝对实相的经验到底是什么呢?”
仍有弟子在进进出出,对这样的会谈他们不感兴趣,对周围的环境,花卉和树木之美他们漠不关心。他们有几个还坐在草地上认真地在听,希望不受过多的打扰。一个有文化的人是不会满足于他已有的文化。
“实相”是无法被经验的。没有途径可到达它,也无文字可以指明它,“实相”它无法被寻找,也无法被发现。寻找以后的发现,,是心灵的腐化。文字的“真理”不是真理,描述不是被描述的。
“古人已经讲过他们的经验,他们静坐时的喜乐,他们的超意识,他们的圣神实相。要是容许有人问,人非得要保留所有这些,和他们尊贵的例子吗?”
静坐的任何权威都是及为否定静坐的。所有知识、概念、例子在静坐里没有地位。完全摈除静坐者,经验者,思想者,是静坐的基础。这种自由是静坐的日常表现。观察者是过去的,他的基础就是时间,是和时间捆绑在一起的他的思想,意象和阴影。知识就是时间,从已经中解脱而来的自由是静坐之花。本不存在什么体系,因而也就不存在真理或着静坐之美的方向。追随他人,追随他的例子,他的文字,就是抛弃了真理。只有在关系的镜像中,你才能看清本然的面孔。看见者就是被看的。没有美德带来的秩序,静坐和其它没完没了的主张,不管怎样,都好无意义,都是毫不相关的。真理没有传统,它无法被传承。
香豌豆花在阳光里愈发的浓郁芬芳。
1973年10月13日
我们乘坐的飞机在3万7千英尺的高空平稳地飞行,机上坐满了乘客。我们已飞过海洋,正在靠近大陆,遥远的下方可看见大海和陆地;乘客似乎有说不完的话,或是不停地要饮料喝,或是翻阅杂志;随后放映一部电影。他们是一群爱喧闹的人,要娱乐,要吃喝;他们睡觉时打鼾却还紧握着手。陆地很快被从地平线到地平线之间厚厚的云块,空间和深度,以及嘈杂的噪声所覆盖。飞机和大地之间,是无尽的白云,飞机的上方,是湛蓝柔美的天空。在靠窗的边角座位上,你完全醒了过来,瞧着窗外变化着的云的形状和照射在云端上那白色的光芒。
意识有什么深度吗?或它只是一个表面的波动?思想可以去想象它的深度,可以声称它有深度,或只是以为它是表面的波纹。思想有什么深度的吗?意识是由它的内容所组成的,它的内容是其整个的领域。思想是外部的活动,在某些语言里,思想的意思是指外部。隐藏在意识层里所具有的重要性,仍然是在表面上的,没有任何深度。思想会给它自己一个中心,就是那个叫“我”的自我,那个中心没有任何深度;无论文字如何华丽,如何巧妙地被组合,都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那个“我”是思想在文字上,在认同上的一个构造;那个“我”在行动中,在现实世界里寻求深度,完全没有意义;它所有的企图是想在关系中建立深度,繁衍它自己意象,而认为他们那些意象的影子是有深度的。思想的活动不具有深度;它的快乐、它的恐惧、它的悲愁都只是表面上的。表面的字意是指有什么东西是在下面,大量的水或非常的浅。一个浅薄或深奥的心灵是思想的文字,而思想其本身是表面的。思想背后的容量是经验、知识、记忆和那些过去了的只是被用来回忆,被遵循或不遵循的东西。离我们很远的下方,地面上一条宽阔的河流在散落的农场之间宽泛的蜿蜒的流淌着,蜿蜒的公路上,汽车如同蚂蚁般地在爬行着。山上覆盖着冰雪,山谷青青笼罩在浓郁的阴影中。太阳直直地晒着,又落向了大海,当飞机着落在雾气腾腾到处喧嚣的变大的城市里。
生命和现实世界里到底有没有深度呢?所有关系都是浅薄的吗?思想能发现它吗?思想只是人类用来开发和强化的工具,如果反对思想是了解我们生命深度的工具的话,那么心灵就会寻找别的途径。过一种浅薄的生活不久便会令人生厌,变得无聊、没有意义,因此会引发不断地去追逐快乐、恐惧、冲突和暴力。如果将思想带来的片断和它们的活动视为一个整体时,那么思想便了断了。当观察者,即思想的片断之一不再活动,总体的领悟才有可能。于是行动是关系,不再导致冲突和悲愁。
只有沉默才有深度。沉默不是思想的运动,爱也不是。这样,光那些文字,或深或浅的失去了它们的意义。爱不可衡量,沉默也是。可衡量的是思想和时间,思想就是时间。衡量是必须的,但是当思想将其引入行动和关系中时,那么伤害和无序开始了。秩序是无法衡量的,唯有无序可以。
海和屋子非常安静,屋后面的山丘,春天里的野花无声地在吐露芬芳。
1973年10月17日
这是个炎热、干燥的夏天,偶尔下几场雨;草地正在变黄,但是长着厚重叶子的大树,却很高兴,满枝头盛开着花。大地好多年未经遇这样的夏天,农场主们非常高兴。在城市里,景象就非常的糟糕,污染的空气,热岛效应和拥挤的街道;粟子树已经开始一点点转黄,公园里到处是孩子们的叫喊声,奔来跑去。在乡下,景色非常优美,田里已宁静下来,窄小的流水天鹅和鸭子在戏水,带来迷人的景象。浪漫主义和伤感主义只被牢固地锁定在城里,而在这乡村的腹地,到处是树木、草地和溪流,到处展现美和快乐的景象。有一条路通往树林,晃动着斑斓的树影,每片树叶、每片枯黄的叶子和草,都握着美。美不是一个文字,一种情感的反应;它不是纤弱的更新于:2023-06-07 13: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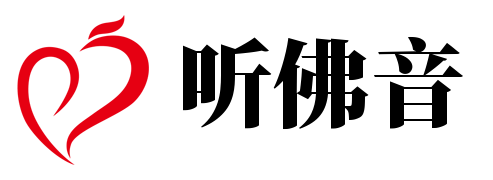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