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日新:永嘉玄觉的山居禅观
慧能禅师门下的另一高足玄觉,他是永嘉(今浙江温州)人,俗姓戴,字道明。关于玄觉的出生,《祖堂集》卷三说他先天二年(公元七一三年)迁化,春秋三十九,依此上推,则玄觉当出生于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六七五年);而《宋高僧传》卷八与《景德录》卷五所载玄觉迁化的年代与《祖堂集》无异,但曰其春秋为四十九,依此上推,则玄觉的出生又在唐高宗永徽六年(公元六六五年)了。玄觉龆年剃髪,以孝行著称,居温州开元寺,并孝养母、姊二人于寺,因而屡遭人诽谤;后来其母亡故,而玄觉仍然未抛弃其姊,以故更遭人诽谤。在这种情况下,有东阳神策禅师①劝玄觉觅师授印。玄觉因于三十一岁那年南行礼慧能禅师,问对契旨,因得六祖印可,遂留曹溪一宿,此后玄觉遂以一宿觉和尚著称(在《祖堂集》卷三,玄觉传的标题就是一宿觉和尚),那则著名的一宿觉公案,成了天下丛林的美谈。对此,《景德录》卷五曰:
(玄觉)后因左溪朗禅师激励,与东阳策禅师同诣曹溪。初到,震锡携瓶,绕师三匝。祖曰:夫沙门者具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大德自何方而来?生大我慢!师曰:生死事大,无常迅速。祖曰:何不体取无生,了无速乎?师曰:体即无生,了本无速。祖曰:如是如是。于时大众无不愕然,师方具威仪参礼。须臾,告辞。祖曰:返太速乎?师曰:本自非动,岂有速耶?祖曰:谁知非动?曰:仁者自生分别。祖曰:汝甚得无生之意?曰:无生岂有意耶?祖曰:无意谁当分别?曰:分别亦非意。祖叹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时谓一宿觉矣。(《大正藏》五一卷二四一页上栏至中栏)
从《宋高僧传》、《祖堂集》、杨亿的《无相大师行状》来看,玄觉在未参慧能禅师之前,便与天台宗的第六代祖师玄朗(公元六七三年~公元七五四年)十分友善,而且玄觉对天台的止观的修学也造诣甚深。据杨亿的《无相大师行状》所载,玄觉在未参六祖以前曾徧探三藏,精天台止观圆妙法门,于四威仪中,常冥禅观。(《中国佛教思想资料汇编》第二卷第四册一四九页)可见,玄觉早就有了相当高深的天台修学造诣,这为他后来的参学六祖,在理论与行持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我们从他的那则一宿觉公案中与六祖的机辩来看,却不曾有一丝天台止观的次第之见,倒是不乏一路向上、直指人心的迅疾机锋,从某种角度上讲,玄觉的机辩真还有点临机不让师的气氛了。而六祖对玄觉的开示则始终是扣住无生这个核心来阐发的,无生这个禅学命题事实上也成了玄觉参悟的鹄的。在玄觉所作的《证道歌》中,几乎俯拾即是表现玄觉这类禅学思想的句子,例如:不因讪谤起冤亲,何表无生慈忍力、自从顿悟了无生,于诸荣辱何忧喜等,即是其例。确实,玄觉自从认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关以后,他虽然居永嘉而近天台之学,但玄觉的一生,终得心于曹溪。
玄觉在六祖那里得法以后,仍回温州弘法,住龙兴寺。杨亿的《行状》说玄觉回温州后,策公乃留师。翌日下山回温江,学者辐凑 (《中国佛教思想数据汇编》第二卷第四册一四九页),号称为玄觉弟子的魏静在《永嘉集序》中也说:三吴硕学,辐辏禅阶;八表高人,风趋理窟(《大正藏》四八卷三八七页下栏)。可见,玄觉回温州后,第一是不再居山而下温江居止;其二是他已经开始了他的弘教生涯,当时学人奔骤其门下,那种门庭若市的盛况是可以想见的。《宋高僧传》也载他有惠操、惠特、惠慈、玄寂等门人,皆传师之法,为时所推(《大正藏》五○卷七五八页中栏),但这些门人此后都不传世了。
玄觉圆寂之后,李邕左迁浙江丽水司马,为他撰写了《神道碑》,自称是玄觉弟子的庆州(甘肃庆阳)魏静为玄觉整理了著作《禅宗永嘉集》,宋初的杨亿为之作《行状》,宋太宗于淳化中(公元九九○年~公元九九四年)诏本州岛重修玄觉的龛塔。玄觉圆寂之后,其盛誉日隆,这恐怕还是因为他留下了一部不朽的著作《永嘉集》吧。关于《永嘉集》的编纂,《祖堂集》卷三载此后所有歌行偈颂,皆是其姊集也(《祖堂集》卷三),那么,现行的《证道歌》等玄觉的作品也许是其姊所纂集了,而《禅宗永嘉集》则可能是出自魏静的编集了。
现存的《永嘉集》思想很不一致,其中几乎表现了两种不同的禅观。其实,这也无须生疑,祇因为玄觉的行状材料不大翔实,我们无从厘清其思想脉路而已,但我们至少也不难看出,玄觉禅学思想的发展很明显地存在着两个阶段:一是未参曹溪前的阶段(即三十一岁前),此时的玄觉与左溪玄朗友善,对于天台禅学也有很深的修养,因而他这一时期的著作则未免不偏重于天台止观之学;二是玄觉参礼曹溪以后这个阶段,此后玄觉接受了慧能的禅学思想,使其思想逐渐地转化为曹溪顿教思想了。因而,现行的《永嘉集劝友人书》以及盛为流传的《证道歌》等作品,就明显地带有后期的思想倾向,而《永嘉集》中第一至第八篇等作品,则比较地倾向于前期的思想。其编纂者大概是为了保存文献之故,一律不加说明地集录到了玄觉的文集之中,因而我们今天看来,就显得前后的思想不大统一了。也许是因为胡适对神会的考证着了名,因而有人准备将《证道歌》的著作权也索性列入神会的门下,其理由是《证道歌》中有对于西土二十八祖与东土六祖的传承记载,还有就是《证道歌》中有不是山僧争人我,修行恐落断常坑这样的句子,因此便将《证道歌》断为神会所作。其实,这种作法也未免太草率了一点,虽然《证道歌》在流传的过程中难免不为后人所增删,使其思想很难保持纯一性,但《证道歌》的主要思想仍然是玄觉的,这是无庸置疑的了。且今天在炖煌的石窟中也发现了玄觉的《证道歌》,像这样一首影响到了西河的禅偈,在流传过程中产生某些变异,恐怕也是在所难免的事情了。
现行的《永嘉集》前八篇循序渐进地阐述了禅修的次第,比较接近于天台的止观之学。第一篇慕志道仪,旨在阐明发心向道、亲近善友等事;第二篇戒憍奢意,重在去掉修行中的懈怠思想;第三篇净修三业,着重谈如何修身口意三业的清净行;第四篇奢摩他颂,主要是谈止的修行;第五篇毘婆舍那颂,主要是谈观的修行;第六篇优婆叉颂,主要谈等持之行,从而离四句、绝百非,达到第十观心门而契玄源者;第七篇谈三乘渐次;第八篇阐明理事不二之理。以上八篇循序渐进,其主要思想脉路似乎是天台家的,但其中也隐含了某些禅宗的顿教思想。如:在三乘渐次第七中,玄觉一方面认为下智观者,得声闻果;中智观者,得缘觉果;上智观者,得菩萨果 (《大正藏》四八卷三九二页下栏),另一方面,玄觉又认为,祇要做到桑田改而心无易,海岳迁而志不移,而能处愦非喧,凝神挺照,心源朗净,慧解无方,观法性而达真如,鉴金文而依了义。如是则一念之中,何法门而不具?(《大正藏》四八卷三九三页上栏)到了这里,似乎并无修行的阶渐次第,而是顿悟一乘妙谛的阐述。
在这里,我们主要想讨论一下玄觉后期的禅学思想,首先,我们来谈谈他的《劝友人书》。《劝友人书》在《永嘉集》中居第九,它集中地体现了玄觉的山居禅观。如前所述,玄觉在永嘉时,与天台宗人左溪玄朗的交谊甚厚,殆在玄觉参学曹溪归来,下温江居止后,玄朗致书玄觉,邀他山居。对此,《宋高僧传》玄朗本传也有记载:
初,觉与左溪朗公为道契,朗贻书招觉山栖,觉由是念朗之滞见于山,拘情于讲,回书激劝,其辞婉靡,其理明白。俾其山世一如,喧静互用,趣入之意,暗诠于是,达者韪之。(《大正藏》五○卷七五八页中栏)
在《永嘉集》第九中,先列出了玄朗的致书,玄朗的信文字不多,悉录如下:
自到灵溪,泰然心意,高低峰顶,震锡常游;石室巌龛,拂乎宴坐;青松碧沼,明月自生;风扫白云,纵目千里;名花香果,峰鸟衔将;猿啸长吟,远近皆听;锄头当枕,细草为毡;世上峥嵘,竞争人我;心地未达,方乃如斯。倘有寸阴,愿垂相访。(《大正藏》四八卷三九四页上栏)
玄朗的致书非但文字优美,亦曲尽其志慕林栖、情耽幽静的禅修思想,它所欣赏的是山居的那种良好的修行环境。诚然,良好的禅修环境对于修行来说,自然是不无裨益的,但也未见得环境就是禅修悟道的唯一条件。也因为玄朗执见于山,未能明了山世一如,喧静互用的妙理,所以,玄觉给他写了一封将近两千字的长信,反复申述此理。
但无论如何说,玄朗终竟不愧为一代禅定修养极高的大德。《宋高僧传》卷二十六载他从如意元年(公元六九二年)至开元十六年(公元七二九年)之间,虽致心物表,身厌人寰,情捐旧庐,志栖林壑。独坐一室,三十余秋,麻纻为衣,粝蔬充食。(《大正藏》五○卷八七五页下栏)对于具有这样能行头陀的禅定修养极高的禅师的复信,自然是难以开晓其妙理的。因而玄觉禅师的复信十分注意措辞的委婉,一来不失道友旧情,二来可以更好地开晓其禅法的了义,反复阐明解契玄宗,以合大道的妙理。玄觉的复信在大致概括玄朗禅师来函的大旨之后,便针对其信中的内容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然而正道寂寥,虽有修而难会;邪徒諠扰,乃无习而易亲。若非解契玄宗,行符真趣者,则未可幽居抱拙,自谓一生欤?(《大正藏》四八卷三九四页上栏)
在这里,玄觉禅师提出了至道本自寂寥,虽有心修为而难以契悟之理,因邪见则无须修习而易染,所以自心未解玄宗,是不可以幽居抱拙一生的。永嘉禅师在这里将禅宗称之为玄宗,也许是禅门中的首唱,此后禅宗的将参禅称之为参玄、称禅宗至道为虚玄大道、提出三玄三要等主张等②,那种以玄喻禅的作法,在后世丛林中也就屡见不鲜了。禅在这里被称之为道,称之为玄,其实也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佛教在东土弘传的历程中,自然得与中国本土的文化相结合。东晋时的僧肇大师可谓善解般若性空之义者,连《高僧传》也称他为秦人解空第一者,更有人称他为中国玄宗大师;南朝的傅大士(相传为玄朗的第六代祖先),曾披衲、顶冠、靸履朝见梁武帝,以表示三教(儒释道)在最高层次上是互相融通的,其《心王铭》曰:观心空王,玄妙难测 (《大正藏》五一卷四五六页下栏),也是以玄来解释佛之至理的。到了玄觉禅师这里,称禅宗为玄宗,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玄觉认为道性冲虚,万物本非其累,在这里,冲虚一语,便是从《老子》第四章中道冲,而用之或不盈(王弼《老子道德经注》,《二十二子》一页中)一语中衍生出来的。可见,以老庄的大道虚玄来喻禅法的非情识可测,多少是含有几分合理性的,同时也不失为弘法的一种善巧与方便。
那么,玄觉禅师何以要告诫玄朗不可幽居抱拙一生呢?因为,深山幽居虽然可以远离凡尘的喧嚣,自然有益于修行;但在另一方面,若一味地执着宁寂的外境,则必将产生一种静妄,也难免不落顽空。玄觉禅师认为:若禅者心未彻了而居山修定,则郁郁长林,峨峨耸峭;鸟兽呜咽,松竹森梢,水石峥嵘,风枝萧索;藤萝萦绊,云雾氤氲;节物衰荣,晨昏眩晃。斯之种类,岂非喧杂耶?(《大正藏》四八卷三九四页中栏)也就是说禅者若心疑未了而入山修定,则必将执着外境而为外境所转,以至于忘失了自心的修习,而使自性迷失。
照此看来,玄觉禅师是有点反对住山的修持了。其实不然,在玄觉禅师看来,住山必须先识道,否则就会执境生迷。因此,他在答信中说:
是以先须识道,后乃居山。若未识道而先居山者,但见其山,必忘其道。若未居山而先识道者,但见其道,必忘其山。忘山则道性怡神,忘道则山形眩目。是以见道忘山者,人间亦寂也;见山忘道者,山中乃喧也。必能了阴无我,无我谁住人间?(《大正藏》四八卷三九四页中栏)
见道后的禅者住山,则人、境双泯,住山而不碍其证道;而未见道的禅者住山,非但无益于修持,反而容易被山境所惑,更添一重迷情。诚然,若禅者能了达五阴性空的话,则自然不会生住山与住世之别了。对此,永嘉禅师认为:若知阴入为空,空聚何殊山谷?如其三毒未祛,六尘尚扰,身心自相矛盾,何关入山之喧寂耶?(同上)若以不二的思想来观之,则真慈平等,声色何非道乎?特因见倒惑生,遂成轮转耳。(同上)永嘉禅师在这里对玄朗执境的破斥,也可谓鞭辟入里了,而其晓人以至道,其语谆谆,纵然是挚友,也不会产生误解了,反而会使之信受奉行。
在此基本上,永嘉禅师的复书向上一路,非但晓其山世一如的平等至理,而且还站在行大乘菩萨道的高度上,奉劝玄朗不弃世法而证出世间法。他认为:
若能了境非有,触目无非道场;知了本无,所以不缘而照。圆融法界,解惑何殊?以含灵而辨悲,即想念而明智。智生则法应圆照,离境何以观悲?悲智理合通收,乖生何以能度?度尽生而悲大,照穷境以智圆。智圆则喧寂同观,悲大则冤亲普救。如是则何假长居山谷,随处任缘哉!况乎法法虚融,心心寂灭,本自非有,谁强言无?何喧扰之可喧,何寂静之可寂?(同上)
若能以般若之智观照境空,则触目菩提,举手举足,市鄽深山,无非道场,这是永嘉在上文中已经表述了的思想内容。然而,玄觉站在行大乘菩萨道的高度上讲,则不能只图个人的自了,而要考虑度他,在永嘉这里,自他是不二的,要做到这一点,也就必须悲智双运了。永嘉禅师的智圆则喧寂同观,悲大则冤亲普救,确实是大乘菩萨道所要躬践实行的,同时也是佛道与禅道修持的最高境界。其实,永嘉禅师的这种禅学主张,早在二祖慧可时便已经提出。《景德录》卷三载慧可大师付法僧璨大师以后,他便随缘任运以弘法了:
(慧可)即于邺郡随宜说法,一音演畅,四众归依,如是积三十四载。遂韬光混迹,变易仪相,或入诸酒肆,或过于屠门,或习街谈,或随斯役。人问之曰:师是道人,何故如是?师曰:我自调心,何关汝事?(《大正藏》五一卷二二一页上栏)
二祖慧可所身体力行的就是这种悲智双运的菩萨道,他随缘住世,弘传正法,拔济世人之苦,而又不染世法。事实上,真正能经得起考验的修持是彻底地的心了,它应当是像二祖这样处世间调心而不被世尘所染的。达到了这种境界,自然就没有山世之别、喧寂之异了。是故《坛经》曰: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法宝坛经般若品》)六祖的旁嗣净居尼玄机,她在习定于大日山的石窟中时,也曾悟到了:法性湛然,本无去住;厌喧趍寂,岂为达邪?(《五灯会元》卷二之本传)对于一个见了性的禅者来说,外境之喧寂自然不会使其心动;而要向上一路,悲智双运,自度度人,则更不会有厌喧趋净之想了。
永嘉禅师的这种山居禅观,非但上契祖师心印,而且也十分合符大乘佛教的精神。永嘉禅师的复书在开示清楚了大乘菩萨道的思想以后,又仍不吝以般若的空观来启发玄朗解黏去缚。他劝导玄朗说:如是则何不乘慧舟而游法海,而欲驾折轴于山谷者哉?故知物类纭纭,其性自一;灵源寂寂,不照而知;实相天真,灵智非造。人迷谓之失,人悟谓之得;得失在于人,何关动静者乎?譬夫未解乘舟,而欲怨其水曲者哉!(《大正藏》四八卷三九四页下栏)永嘉禅师认为:祇有真正彻了的禅者,方能住世住山,均会任运随缘而不受情之所牵挂。为此,玄觉的复书收束曰:
若能妙识玄宗,虚心冥契;动静长短,语默恒规。寂尔有归,恬然无间。如是则乃可逍遥山谷,放旷郊鄽;游逸行仪,寂怕心俯;恬淡习于内,萧散扬于外。其身兮若拘,其心兮若泰;现形容于寰宇,潜幽灵于法界。于是则应机有感,适然无准矣。(《大正藏》四八卷三九四页下栏)
在这里,永嘉禅师又重复地提到了玄宗二字,以玄喻禅,非但谐音,而且也可以体现禅旨的深邃莫测的特质。正如我们上文所述,在永嘉的禅观中融摄了老庄的思想,而且在他的复书中甚至还有若知物我冥一,彼此无非道场的语句,则似更富有魏晋以来的玄学情韵。然而,归元性无二,方便有多门,若不熔冶东西土文化于一炉,焉能使不可言说的禅法有弘传的方便?若站在方便的角度上讲,玄觉的这种作法,何尝不是一种无碍的慈悲。更何况以这种方便来弘化,易于破斥对方的境执(即对山居环境的法执),使之反观自性,顿悟禅旨,从而将物我打成一片,使山市之境皆同一如而不生喧静之心呢!
我们在对永嘉山居禅观作了粗浅的阐述之后,还想对他的《证道歌》作一些简单的介绍。《证道歌》通篇以唐代民歌的形式出现,全篇共六十二节,表现了玄觉比较丰富的禅学思想。其中包含有入深山,住兰若,岑崟幽邃长松下;优游静坐野僧家,阒寂安居实潇洒的山居之趣,在那种境界中,江月照,松风吹,这可真是身居闹市的达官贵人们所难以享受的一种清福了。其中自然也有玄觉对他早年经教修学的反思,他认为:吾早年来积学问,亦曾讨疏寻经论;分别名相不知休,入海算沙徒自困。却被如来苦呵责,数他真宝有何益?(《证道歌》收在《大正藏》四八卷三九五下栏至三九六下栏,此处所引《证道歌》皆出北京刻经处本,以后不再一一注明,仅于引文后注明节次)从这里可以玄觉对他原来那段徧探三藏的修学经历的反思,也说明了他从此以后已经朝着禅门顿悟的方向精进了。也因为玄觉的禅学思想产生了转变,使得他过去所学的经论也一时融通,达到了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的境界,这一境界对于宋儒理一分殊思想的建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下面,我们想就《证道歌》略从两个方面作些介绍。
我们之所以认定玄觉是出自曹溪门下,最重要的一点恐怕还是因为他的《证道歌》所倡导的是禅门顿教思想。自然,禅门的顿教思想,是建筑在佛性皆有这一理论基础之上的,也因为佛性皆有,因此一旦见性了也就会顿然开悟。玄觉对于禅学思想的阐发是非常透彻的,他认为:
摩尼珠,人不识,如来藏里亲收得。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颗圆光色非色。[第八节]
穷释子,口称贫,实是身贫道不贫。贫则身常披缕褐,道则心藏无价珍。[第十一节]
心镜明,鉴无碍,廓然莹彻周沙界。万象森罗影现中,一颗圆光非内外。[第二十八节]
以上三节,分别阐述了佛性具足的思想。玄觉在这里借用了摩尼珠、道、心镜、圆光等譬喻,以说明众生本自具足的真如觉性,显得十分得体。我们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玄觉的家境不佳,他原来住温州开元寺时,因赡养其母、姊而屡遭人诽谤。因此,作为玄觉本人来说,他肯定是身贫的,但他认为道(自家摩尼珠)是不贫的,他的这种境遇自然也在促使他朝着禅宗的顿教法门中勇猛精进,去探取这个宝藏。也因为佛性人人具足,这就为顿悟成佛提供了理论基石,《证道歌》在此基础上大倡禅门顿教思想。
《证道歌》在开篇就说:无明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化身;法身觉了无一物,本原自性天真佛。[第一节]他一开头就向读者抛出了顿教思想,接着,又对这一思想作了更为透彻的阐述。《证道歌》说:
顿觉了,如来禅,六度万行体中圆。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第三节]
弹指圆成八万门,刹那灭却三祗劫。一切数句非数句,与吾灵觉何交涉?[第三十六节]
从这些对于大乘顿教思想的阐扬来看,足以见出玄觉最终是得法于曹溪的了,这在我们分析他的《劝友人书》时,也已经涉及了这一命题。玄觉的顿悟思想是有理论依据的,这大抵与他原来所具有的甚厚的经教修养这一点十分相关。他在《证道歌》中也曾提出了是则龙女顿成佛,非则善星生陷坠,其中的龙女成佛,典出《法华经提婆品》,当时的龙女才八岁,但她能受持诸佛所说甚深秘藏,深入禅定,刹那顷发菩提心,得不退转。当年三祖僧璨在开示道信禅师时,也曾援引过这个典故,玄觉继之而用此典,遂将禅门刹那而成正觉的教理作有力的了阐扬。
《证道歌》在另一方面则是阐扬般若性空之义,然后援此展开对二执、毁誉、定慧、果报等一系列禅学方面命题的讨论,从而将之纳入无住性空的本体之中。《证道歌》说:大丈夫,秉慧剑,般若锋兮金刚焰[第三十二节],事实上,这就点明了玄觉对《金刚经》的依持,因而从某种角度上可以见出五祖付嘱慧能时,采用《金刚经》应当是信然不诬的。况且,玄觉在《证道歌》中也开宗明义地说:有人问我解何宗?报导摩诃般若力,这就进一步明确了玄觉对般若性空思想的遵循,这自然也与曹溪以来的思想一脉相承。众所周知,《金刚经》等大乘般若类经典,对于外相的破斥是干净彻底的,而破斥外相这一原则也成了《证道歌》所表述的重点。在《证道歌》中,几乎处处可以发现玄觉对二执的破斥,他认为:证实法,无人我[第二节],这便是对人我法的破斥;又曰:不求真,不断妄,了知二法空无相。[第二十七节]又曰:不可毁,不可赞,体若空虚勿涯岸。[第三十七节]又曰:取不得,舍不得,不可得中只么得。[第三十八节]在这里,玄觉对于真与妄、毁与誉、取与舍等二执边见,一一作了破斥,自然,玄觉对于二执的破斥,其旨在彰显无相之理(亦即般若实相义)。因此玄觉认为:觉即了,不施功,一切有为法不同。住相布施生天福,犹如仰箭射虚空。势力尽,箭还坠,招得来生不如意。争似无为实相门,一超直入如来地。[第二十二、二十三节]在这里,玄觉所阐明的是无相妙理,而所举的例子也是人们所常见的布施之类的事情,他从无相布施的角度,阐扬了无为法的甚深妙义。
在开显了般若的无相妙义之后,玄觉对于禅门所不可回避的禅定等学也作了一定的阐述,他认为定慧圆明不住空,应当是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第十九节]。这种行住坐卧皆是禅之妙用的禅修思想,既是发祥于曹溪的慧业,更是洪州一系禅者们所极力阐扬的。可见,玄觉的禅观与湘赣地区禅者的禅学主张基本上是相通的。
《证道歌》既然阐明了无相的妙义,那么它对于人们寻常见到的毁誉等事又将如何看待呢?这个问题也是玄觉一生感受最深的,他早年在温州开元寺时因赡养老母与姊姊,屡遭人毁谤,其人情之难受,他是深有体验的。但因为他以甚深的般若空观来照破,所以在那种极其难以忍受的境遇中,他坦然挺了过来,成就了他一生的慧业。对此,《证道歌》是这样说的:
从他谤,任他非,把火烧天徒自疲。我闻恰似饮甘露,销融顿入不思议。[第十四节]
观恶言,是功德,此即成吾善知识。不因讪谤起冤亲,何表无生慈忍力?[第十五节]
对于毁谤,玄觉能用这样一种心量来对待,可以说真正达到了无生法忍的境地,这自然也是契于无相妙义的了。但这毕竟是玄觉对待别人毁谤他的心态,换言之是玄觉在接受别人毁谤时的心境。若是有人毁谤佛法,玄觉的态度则大不如此了,他十分坦诚地告诫世人:欲得不招无间业,莫谤如来正法轮[第四十五节],从这里就可以充分地见出玄觉的那份护法心了。
同理,从般若无相的境界出发,玄觉对于佛教中所常说的果报等观念,也一一作了阐述。他站在无相的最高境界上提出了了即业障本来空,未了还应还旧债[第五十四节]的总体观点,号召人们精进修行,了却无量劫的夙业。但是,站在佛教传统的戒律上来说,又有定业难转之说,因而玄觉特地指出:有二比丘犯淫杀,波离荧光增罪结。维摩大士顿除疑,犹如赫日销霜雪。[第五十七节]玄觉在这里引用了《维摩经弟子品》中的典故:当时,有两个比丘因无心而犯了淫杀的重戒,便去找优波离释疑悔,优波离便按照戒律为他们开示,谁知反而增重了他们的罪障。后来,维摩居士随即为他们开示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之理,使这两个比丘当即得到了解脱(参见《大正藏》一四卷五四一页中栏)。玄觉举这种例子来说明了即业障本来空的妙理,无疑也是对大乘顿教思想的合理发挥。《证道歌》的内容很丰富,我们在这里仅是提出了其中主要的禅学思想,略作分析而已。
总之,玄觉的禅观虽然受了天台家的思想影响,但从其整体来看,他仍然不失为曹溪的弟子,尤其是在他后期接受了曹溪顿教思想以后,曾对天台的教观作过一番深邃的反思,从而更为坚定地朝曹溪路上精进。另一方面,他以曹溪思想去包容天台教观,因而使得他在曹溪的门人中,其禅学思想自成一格。后世法眼宗的天台德韶禅师,就走上了永嘉的这条圆融禅、台二教的道路,再发展到其门人永明延寿禅师那里,则大有将佛教各个宗门圆融起来的气量,而追溯其理论源头,似乎还是源于玄觉禅师这里。
* * * *
在神会、慧忠、玄觉这三位曹溪门人中,神会一生奔波,他虽然在授徒弘化的影响方面遍及中原,其门人中也有皎皎者(如慧坚、宗密等)出世,但荷泽宗毕竟在与北宗的抗争中互相销融了。慧忠一生虽然荣为国师,门人上万,可惜无一神足能弘扬其法,故其禅法传至耽原而终。玄觉住世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的禅观颇具特色,可惜其后嗣也是不荣。但他那不朽的著作《永嘉集》至今仍为禅门所推崇,也可谓将一代禅匠的思想传于后世了。
--------
① 神策禅师在《景德录》卷五中作玄策禅师,他是婺州金华(今浙江金华)人,出家后游方,得法于六祖慧能。
② 参玄,在石头希迁的《参同契》中称参禅为参玄,有谨白参玄人,光阴莫虚度之句(见《景德录》卷三十)。虚玄大道,曹山本寂在诠释洞山的《五位旨诀》时曾说:兼带者,冥应众缘,不堕诸有,非染非净,非正非偏,故曰虚玄大道,无着真宗。(见《曹山语录》与中华书局一九八四年版《五灯会元》卷十三七八七页)三玄三要是临济义玄所提出的,他认为禅师在接引学人时,一语须具三玄门,一玄门须具三要,有权有实,有照有用。(见《临济禅师语录》)他的后世门人善昭曾就此作颂,以阐扬义玄的三玄三要法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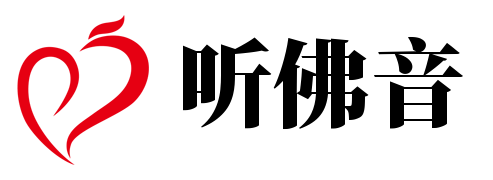

发表评论